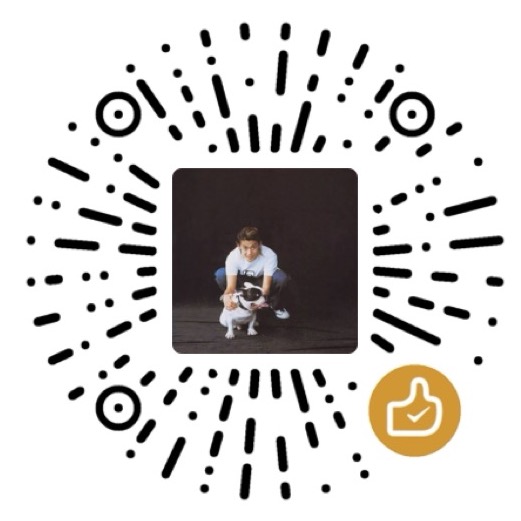我们当下的媒介使用习惯,是否在很久以前就养成了?
本文首发于腾讯新闻 全媒派 。
为什么键盘上的字母按照QWERTY的顺序排列?为什么计算机编程总喜欢“Hello, World”?为什么电视剧时长通常为每集45分钟?为什么高铁座位分布是ABCDF却没有E呢……以上种种问题,都可以用“路径依赖”理论(Path-Dependence)加以解释。
普遍意义上,路径依赖是指一旦选择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进而沿着既定方向持续前进。这一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Paul David在1985年提出,后因美国经济学家Doglass North借该理论阐释经济制度演进规律而扬名。1
通俗地讲,“路径依赖”可以被理解为传统惯习的力量,过去的经验被应用于新的情境之下,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
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路径依赖”或“传统惯习”现象,甚至不被我们所察觉。当我们把视野进一步纵向拓展,这些习惯可能来自互联网初期、来自电视或印刷时代,或是更为久远的传播史早期。
本文从路径依赖的理论出发,希望去发现和理解网络生活中的此类现象,并进入媒介演进的视野,探索过去如何影响现在,甚至持续地影响着将来。
信息生活里的路径依赖现象 #
1868年,一位名叫Christopher Latham Sholes的美国出版商为打字机模型申请专利,并于1874年成功将商用打字机投放市场。
在这六年间,打字机键盘上的字母顺序几经变换,从“ABCDE”到“QWE.TY”,再到“QWERTUIOPY”,随后又调整了“Y”的顺序,最终固定为“QWERTY”。2
这一字母顺序借助打字机的行销逐渐成为打字员的习惯,进而延续至今,出现在我们使用的电脑键盘上,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路径依赖”。
同时,也有批评者认为QWERTY的布局并不符合使用习惯,因此,旨在提升打字效率的Dvorak键盘于1936年问世,但还是没有影响到前者的主导地位。
类似的,程序员学习计算机编程似乎总是以“Hello, World”开始。1972年,贝尔实验室成员Brian Kernighan在 A Tutorial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B 一书中首次提到这个字符串。
其后“Hello, World”被当作案例出现在 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 (1978)中,随着教材的畅销,“Hello, World”也备受欢迎并逐渐成为各类编程语言的“第一课”。3
其实某种意义上,社交媒体本身也不算是“新鲜事物”。古罗马时代庞贝古城的岩壁上,就写着“不管是谁,想写就写”。
在媒体人Tom Standage看来,经历了报纸、广播及电视等的大众传播媒介时代,社交媒体不过是恢复了“Writing On the Wall”的传统,让莎草纸或咖啡馆的古老社交属性,在网络世界中再次复活。4
总之,“路径依赖”会让最开始的偶发事件,不断自我强化成为一种强硬的事实,但也会因时代环境的变换,在自身中创新和突破,这在媒介演进中尤为明显。
在印刷时代,“文首空格”是为了节约纸张,同时在段与段之间制造停顿,方便人们阅读理解。
如今,网络页面的文字呈现则是“左右对齐”,而刻意加大的段间距或空行表示间隔的排版方式(本文就是如此),则取代了文首空格的分段功能。
句子变得愈来愈短,图片越来越多,如果反过来用这种方式去制作书籍,结果就是页数增多,书变得更笨重。
45分钟的电视剧集,起源于只能容纳15分钟的胶片卷盘。胶片电影的时长也通常为90分钟或120分钟(15的倍数)。
无独有偶,一首歌也因为黑胶唱片的容量限制必须控制在5分钟之内。5然而,随着数码记录媒介的流行,时长限制似乎成为了过去式。
尽管一部分音乐或影视作品依然延续着过去的时长,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内容正在挑战着受众的忍耐极限。
此前我曾探讨过复古元素在当下内容消费环境中的回潮,这种复古潮相较于“路径依赖”的强延续性,似乎只是短暂的、点状的一次次“回眸”,而内容呈现和内容消费的“路径依赖”,则像是海浪中漂泊的船所找寻的灯塔,无论形式如何变化,有些细节始终锚定着。
如何理解媒介演进中的路径依赖? #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当下媒介环境(或者更为具体的网络信息传播环境)中的这些“路径依赖”现象呢?
从个体角度而言,我们或是因为习惯,或是因为便捷,而选择了那些熟悉的媒介使用方式。
在儿童时期习得的能力、养成的习惯,通常难以遗忘或改变,甚至会伴随一生。从媒介学的视角下去理解“个人”,就要去思考我们成长中所浸淫的媒介环境。
以90后为例,出生在1990年代,经历了电视最后的辉煌。这一代人也许不太愿意接受尼尔·波兹曼式的批评,不愿意把自己比作“沙发土豆人”,却可能时常怀念电视作为共享媒介将一家人聚集在一起的温馨场景。
21世纪的新生代们,则出生在互联网制造的“地球村”里,他们是网络原住民,是从小就会打开手机寻找动画片、解锁iPad玩游戏的一级“冲浪手”。
电子阅读淹没印刷书籍、网络通讯替代现场交流,也变得司空见惯。他们把网络作为“常态化”生活方式,也不会乐意接受来自电视时代的“规训”。
这么看来,卢德分子(英语Luddite,意指仇视新奇发明的人)怒砸机器,所维护的不仅是熟悉的工作方式,还包括自己存在的意义。
我们很难去畅想下一代媒介的使用习惯,但回过头看,短视频的上下滑动,似乎和电视遥控器上下按键切换频道的行为习惯,有着潜在的联系。
音乐APP左右切歌,和CD机上的物理按钮,也存在延续性。或者转换下视角,习惯了用手指触摸手机,不经意去点击不支持触屏的电脑或电视屏幕,也是当下在所难免的事情。
在社会层面,“路径依赖”可以理解为对过去经验的继承、对传统惯习的延续、对集体记忆的传承。
一个人有自身的个人习惯,一个社会也有其传统惯习。任何媒介的发展、媒介环境的生成,除了个体参与和技术更新,都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正如前文提及的示例,互联网环境中的这些路径依赖现象,各有各的历史,有的可以追溯到互联网初期,有的来自电视或印刷时代,或是更为久远的传播史早期。
互联网环境中社交媒体像是用新的技术复现过去的“传播梦”:“博客是新型的小册子,微博和社交网站是新型的咖啡馆,媒体分享网站则是新型的摘记簿。”6
当下流行的播客传承了口语文化。广播是大众传播时代的产物,话筒背后是播音员,而播客把话筒还给了普通人。广播是扩音器式的共享媒介,播客则更私密地对话。
Newsletter(新闻信)传承了手写传播形式,手写传播最早出现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城,后在欧洲广泛流传。如今,以邮件订阅等形式存在的Newsletter,算得上是喧嚣互联网中的一隅“清流”。以上种种都可以视为历史的回归,或对传统的延续。
“社会需要‘过去’,首先是因为社会要借此来进行自我定义。”7 路径依赖行为从过去寻找依据,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媒介现实。
反过来讲,社会希望创造何种媒介环境,也就会选择何种“过去”去发现和重构。媒介技术既有“路径依赖”,也有突破创新,最终,新媒介和旧媒介融合发展。
媒介技术的变革中,新媒介一方面生成新的内容,一方面用不同方式来传播旧内容,往往会出现“新瓶装旧酒”的路径依赖现象,“电影改编舞台剧、收音机重播演出实况,以及电视台重播旧电影的现象比比皆是”。8
借用刘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提出了技术发展中的“假晶”现象9,我们会发现,尽管新媒介正在不断刷新着我们的使用方式和生活习惯,但旧媒介依然试图抓住话语权,新媒介成了维护旧媒介秩序的手段,甚至必须依赖于旧媒介而发展,这也可以视为路径依赖。
然而,技术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力量,往往会挣脱路径依赖形成的社会运行惯性。新媒介技术总会在意想不到的角落创造性地喷薄而出,带来媒介技术应用的突破和创新。
同时,媒介技术的发展往往会打破垄断局面,印刷术打破了精英阅读,提升了社会的识字率,带来了大众阅读。社交媒体打破了专业机构的内容生产,让人人都有了“麦克风”。
路径依赖的反思与展望 #
“路径依赖”的提出,往往伴随着对其自身的批判。走老路、因循守旧、丧失活性等词语,无不是对“路径依赖”不同程度地挖苦和否定。
这是因为当习惯了用传统经验去解决现实问题,就容易产生惰性,一方面不利于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还会制造出新的问题。
我们经常提及信息茧房或过滤泡泡,是放在内容信息层面理解的。但从代际角度去思考,过滤泡泡则可以被理解为“代沟”。
不同代际之间因为成长中的媒介环境不同,往往会共享不同的经验和记忆,产生不同的媒介习惯,进而制造出了各自的“话语”。
纸媒环境下的人也许会更偏爱严肃阅读,网络原住民可能热衷于短视频,人们只是延续了自身的媒介习惯,但还是会造成代际之间的差异。
譬如,年轻人聊天框里的微笑EMOJI已经失去了其本意,而是一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表情,这可能不被长辈们理解。
但就像十年前的网络热梗都已被历史的灰尘掩盖,当前的习惯会延续多久,同样不得而知。
或许这也将成为我们这代人的“集体记忆”,成为我们可以在社交生活中彼此理解的“暗号”。
不过,路径依赖也有其自身的价值,这是需要珍视的。当王心凌的一首《爱你》唤醒了80、90后们的青春回忆,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孤勇者》也会激发出长大后的孩子们的集体共鸣。
过去经验、传统惯习或集体记忆,可以理解为社会的保持器,帮助社会成员产生群体归属感,具有确立身份认同或社会认同的重要功能。
从时空角度来看,它们会为社会成员提供整体想象和历史意识,具有共享文化意义、传承文化传统的功能。
这已经超越了路径依赖的范畴,而关乎一个社会如何记忆它自己。
张卓元等:《政治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 ↩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2200664-the-truth-about-the-qwerty-keyboard/ ↩
https://www.thesoftwareguild.com/blog/the-history-of-hello-world/ ↩
[美]汤姆·斯丹迪奇:《社交媒体简史:从莎草纸到互联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 ↩
成都商报:《为什么电视剧45分钟一集》,2014年11月29日, https://e.chengdu.cn/html/2014-11/29/content_499344.htm ↩
[美]汤姆·斯丹迪奇:《社交媒体简史:从莎草纸到互联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 ↩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
[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 ↩
[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