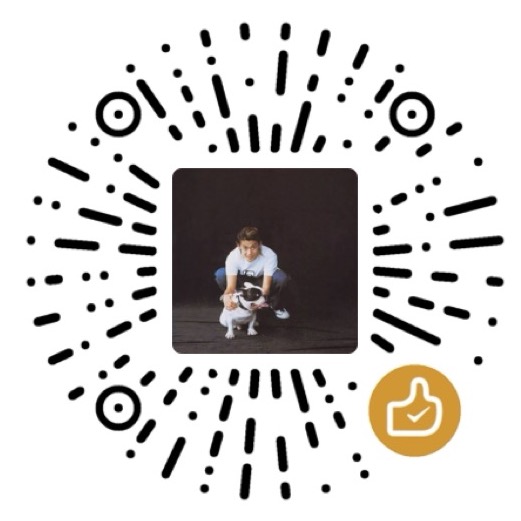“这一切我都要”:韩炳哲的痛苦宣言
倦怠社会、功绩社会、愤怒社会、积极社会、透明社会,以及妥协社会、生存社会……韩炳哲对当下社会做出了许多简要界定。这些词语彼此牵连、网状延伸,指向不同面向,构成了当前我们个体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形容词。
在《妥协社会》(The Palliative Society,或无痛社会、舒缓社会)中,韩炳哲以云格尔《论痛苦》为起点,谈论痛苦及其背后更为宏大的否定性在现今社会中的消亡或掩盖。认为当下是一个“妥协社会”,遍布痛苦之恐惧,人们厌恶死亡、限制、惩罚等一切负面因素,渴求健康、积极、自由、实现,并愿意为之自我牺牲、自我剥削。
痛苦成为“医疗事件” #
在前现代的酷刑社会,“痛苦被当作统治手段”,在福柯式的规训社会,痛苦不再被公开展示,而是退入监狱、军营、疗养院、工厂或学校等封闭的规训场所。
到了当下的妥协社会、功绩社会,戒律、禁令或惩罚等否定性让位于动机、自我完善或自我实现等肯定性,痛苦成为“医疗事件”——肉体上的疼痛可以使用止痛剂或麻醉药;精神上的疼痛则指向心理状态,焦虑、痛苦、抑郁都可以放置在心理学上进行研究和医治。
然而,在韩炳哲看来,痛苦在这一过程中,局限在医学领域,成为单纯的身体上的折磨,失去了象征性和诗意,失去了叙事的可能。
如果社会没有痛苦,那么“幸福也会变的乏善可陈,成为一种沉闷的舒适状态”;“真理”也就不复存在,社会如同一座同质化的地狱(或“妥协的舒适区”)。对于个体而言,“我们既没有爱过,也没有活过”,更失去了彼此之间的共在与关联。
痛苦为何被掩盖、消失和恐惧? #
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当下社会整体表现出一种对肯定性的拥抱以及对否定性的摒弃。
韩炳哲认为人对自身的确立来源于对他者的否定,这个他者对自身产生攻击,如果不否定他者,就会迎来自身的毁灭。这一观点可追溯到黑格尔在主奴之辩中强调他者对自我主体性型塑的必要性。
然而,社交媒体或流媒体利用算法生成“同好”,不断制造相同者的同时也是在驱逐他者。资本主义也把效率和金钱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标准,所有人纳入了一种评判体系。
他者的否定性给同一者以轮廓和尺度。随着他者被驱逐、被厌恶,没有了这一否定性,同质化便会滋长。
人们关注“立刻”的数字化之物,而否定“漫长而迟缓之物”;爱欲(Eros)已经死了,只留下了自恋以及物化为性爱对象的消费型的爱;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个体的人成为“功绩主体”和自身的雇主,在幸福的信仰中,关注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自愿剥削,陷入倦怠。
这其中,痛苦自然也“被看作虚弱的象征”和“被掩盖或优化的东西”,进而“被剥夺了所有表达的机会”。在简中语境,负增长、慢就业、待富者,新词背后的思维范式正对应着“痛苦恐惧”,对负面的、否定性的一切进行消除和掩饰。
“点赞社会”和“讨喜文化” #
为了消除一切痛苦和否定,“赞”成为当下的止痛药。不管是社交媒体上的“Like”按钮,还是社会生活中的“能够”导向,这一“我喜欢”的逻辑,不断从社交媒体延伸至文化领域,形成“讨喜文化”。
韩炳哲认为,讨喜文化的成因之一在于“文化的经济化和商品化”,文化产品陷入消费主义逻辑,首先是讨人喜欢的形式,即向消费者承诺文化与美学体验,样式重于使用价值。
可以想象,越来越多的书籍封面成为一种海报式的张贴画,越来越多的商铺或风景成为打卡点,向每一双眼睛和镜头张开双臂,渴求在网络上无限复制。
在讨喜文化之下,艺术和消费领域混为一谈,艺术利用消费美学,变得讨喜。
阿多诺认为,艺术是“对世界的陌生化”。鸡皮疙瘩是“最初的美学画面”。但当下各种消费品、奢饰品与艺术家的联名款,却是讨喜和舒适的,艺术不再使人诧异、扰人不安、惹人心乱,失去了陌生感带来的“光晕”。
也难怪艺术史学者徐小虎直言不讳:
假的艺术家只是做买卖,除了名气就没什么了。村上隆、草间弥生不是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没有任何灵魂的价值。
直面痛苦的价值 #
即使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或者数字化工具再发达,我们的生活都应该是“讲述”而非“计数”。沉浸在虚假的快乐中,生命不再鲜活,而被囚禁于同质化的地狱。
正视痛苦,并非是要忆苦思甜,或者制造痛苦。而是要去理解痛苦,以及负面的、否定的本身都有其各自的价值,这是人本身的完整性和主体性所在,否则我们是虚假的、片面的、同质化的、单向度的。
我想,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恰如其分地呼应了这一思考。
野蛮人约翰说,“你们只是消灭苍蝇蚊子,消灭所有不愉快的东西,而不是去学会忍受它们。”他说,“我要的不是这样的舒服。我需要上帝!诗!真正的冒险!自由!善!甚至是罪恶!”
这时候,总统反问道,“那你是不是也需要衰老、丑陋、阳痿、梅毒、癌症、饥饿、伤病这些丑陋的东西,甚至你也希望总是在担心明天有不可预知的事发生,或者你还需要遭受种种难以描述痛苦的折磨呢。”
野蛮人说,“这一切我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