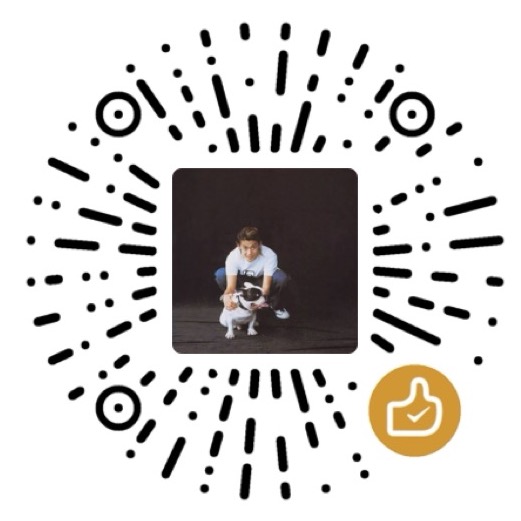媒介事件与媒介仪式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认为宗教以两种方式代表着社会现实:一方面,他们为社会成员解释社会现实提供了必要的认知方式。另一方面,宗教实践如仪式,在表达社会现实上,形成了重要的、为全社会接受的标准化和可重复的方式。宗教的公共仪式向个人提供了归属感,加强了个人同他所属社会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实现社会整合。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到来,科学接替宗教成为了社会成员的主要认知方式,在涂尔干看来,尽管宗教仪式在社会整合上是不可缺少的,但终将走向衰落。
新涂尔干主义者发展了涂尔干的观点,他们认为尽管宗教举行的“神圣的”仪式会衰落,但生活中“世俗的”仪式将会履行集体认同和社会整合的功能。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就是两位具有代表性的新涂尔干主义者,他们在《媒介事件》1中,不仅着眼于公共仪式和社会事件,还提出了媒介的中介性,认为社会成员在无法直接交往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媒介聚集在一起,并认识到他们相互之间构成了社会整体。
媒介事件 #
1980年卡茨在《媒介事件:在场的感觉》中首次提出“媒介事件”(media events)这一词语。几年后,他与戴扬合写发表《竞赛、征服、加冕:论媒介事件及其英雄》,“媒介事件”开始在西方传播学界流行。1992年,两人进一步拓展内容,出版了《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一书。卡茨的导师拉扎斯菲尔德是传播效果研究的开创者,《媒介事件》这本书从实质上来说即是一本讲述媒介效果的书。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肖尔评价这本书“对电视直播现象作为强大社会力量进行了全面探索与准确勾勒,是理解电视如何影响受众的奠基之作”。
在卡茨和戴扬对“媒介事件”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媒介事件首先是“非常规性”的,它们“是对惯常的干扰,干扰着正常播出乃至生活的流动”。其次,媒介事件还是“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的”,典型的事件组织者是媒介与之合作的公共机构,比如政府、议会、政党或国际机构等。再次,媒介事件经过电视媒介的播出,“把事实从其发源地剥离出来”,并“在崇高和礼仪的氛围中完成的”。最后,媒介事件其实就相当于“重大仪式事件”,而那些没有提前策划的事件的直播(如核泄漏事故、肯尼迪被刺事件)只被看作是“重大新闻事件”,虽然两者很相似,但“重大新闻事件将求偶然性、突发性;重大仪式事件则崇尚秩序及其恢复”。
这么看来,“媒介事件”也可以被称为“媒介仪式事件”或“媒介仪式”。而正是由于“媒介事件”有挥之不去的“仪式”的魅影,卡茨和戴扬才被看作新涂尔干主义者。
在对媒介事件进行划分时,卡茨和戴扬提出三种类别:竞赛、征服和加冕(3C:contests,conquests,coronations),并把这三种类别与马克斯·韦伯的三种权威类型对应:合理性、超凡魅力和传统。“竞赛”类媒介事件包括的范围,可以从世界杯到总统竞选辩论,也可以从奥运会到参议院“水门事件”听证会,主要有体育和政治两大主题。“征服”类媒介事件比如外交事件、登月航行等,体现出“人类的巨大飞跃”,因此发生及其效果都是罕见的。前面的“竞赛”和“征服”都包含很强的仪式成分,而“加冕”类媒介事件在卡茨和戴扬看来,完全就是仪式,比如婚葬典礼、将军加冕、奥斯卡颁奖等。
然而,正是对媒介事件的此般界定,成为了被后来研究者紧抓不放的弱点。批评者认为这一界定过于主观和严苛,分类也过于狭隘,后果局限于积极方面。大卫·科泽在《仪式、政治与权力》中写道,“仪式研究的传统涂尔干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冲突。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仪式在制造政治变迁上的作用,因为仪式的作用被认为是巩固已存在的社会系统。“他认为既要看到的仪式对社会团结的巩固作用,也要看到仪式同样可以被反对派所用,进而带来对旧制度的革新与超越。
威曼反对媒介事件总是充满积极影响,他将“恐怖事件”列入媒介事件,认为恐怖事件是恐怖分子提前策划的媒介事件,他们企图通过吸引媒介报道,以引起世人关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媒体成为了恐怖分子的帮凶。凯瑞提出“驱逐仪式”,认为驱逐仪式向公众展示了“社会暴政”,强化了社会差异观念,而非社会整合。利比斯以以色列发生的系列自杀式汽车爆炸案位列,将此类策划性的灾难事件纳入媒介事件范畴。2007年,卡茨不得不做出回应,发表了《No More Peace How Disaster Terror and War Have Upstaged Media Events》2。在文中,他对媒介事件的界定进行了修正,并将恐怖袭击、灾难和战争的媒体报道纳入“破坏性”媒介事件。
2008年戴扬反思其原有媒介事件概念时,指出形势在变,媒介事件也在变。他首先分析了媒介事件概念的延续性,现今媒介事件延续以往媒介事件四个特征:破格强调、演练示众、认信效忠和共享体验。“破格强调”指事件的媒介直播无所不在,打破日常规律及反复播放强调。“演练适中”指媒介事件无关平衡、中立和客观,而是主观建构真实的姿态表演。“认信效忠”意为接受和传递组织者对事件所下定义及其中所载核心价值观。最后,媒介事件不仅提供信息、知识和观念,更是一种“共享体验”,是对“我们”的建构和重构。
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媒介事件的界定还会受到进一步的质疑。全球性报道日趋增多,从而变成了国际性事件。这样,媒介事件的边界(国家级事件)便受到挑战。而来自互联网的挑战,则表现在媒介事件的效果上。虚拟空间中,多元化的观点和碎片化的个体似乎成为了社会整合的阻碍。3
媒介仪式 #
事实上,新涂尔干观(Neo-Durkheimian)有两个版本,卡茨和戴扬代表的“媒介呈现既有的仪式”属于其一。另一个版本则不那么关注这些不寻常的媒介事件,而更为关注媒介本身,特别是电视在把社会生活组织为一个整体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换句话说,观众在特定时间打开电视、观看节目,这就已经可以被视为一种仪式。尼克·库尔德里在他的《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4中,对另一个版本表示认可,但此后,他对“媒介仪式”的探讨却又走了另一条路径:后涂尔干观(Post-Durkheimian)。
库尔德里认同莫里斯·布洛克和皮耶尔·布尔迪厄的观点,认为仪式并不在于确认我们共同分享了什么,而在于巧妙处理冲突和掩盖社会不平等。遗憾的是,在媒介分析中,每次“仪式”都被放在一个相当传统的语境中(即涂尔干的社会整合仪式观)。仪式的功能被看作确认一个已经建立的、多少是自然而然的并且毋庸置疑的社会秩序。
在后涂尔干观中,媒介仪式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与“媒介本身”相关联的先验的价值观上,即媒介“自封的”代表整个社会的能力。这个能力的背后就是日常生活中类别化的模式,这些模式的最终效力就是把媒介“里”的事物高于不在媒介“里”的事物这一等级结构自然化。因此,库尔德里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问题:媒介如何使得自身作为社会中心的自身合法化、自然化,并通过什么手段来维持强化这样的差异性地位。库尔德里通过对媒介朝觐、现场直播、媒介监视、媒介化的自我表露等部分的论述,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解答。
在媒介仪式的定义上,库尔德里不再从卡茨和戴扬的“媒介事件”生发,而是进行了全新的界定:“围绕关键的、与媒介相关的类别和边界组织起来的形式化的行为,其表演表达了更广义的与媒介有关的价值,或暗示着与这种价值联系”。在库尔德里的整个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只是抽象出仪式的作用,而不再执着于仪式的外部的特征,媒介仪式也就成了媒介作为一种被自然化、合法化的社会中心,所进行的行为活动。
库尔德里在《媒介仪式》中,还提出了“关于媒介中心化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mediated centre)。媒介仪式这让普通人卷入到中心的浪潮之中,进而感受到社会的团结凝聚(尽管有可能是虚假的)。这和曾经的宗教或王权作为社会中心后,进行的仪式行为发挥的作用同质。这么理解之下,宗教、王权或媒介,都是“中心化”的继承者,在人们用民主推倒了宗教和王权的压迫后,媒介成为了新的掌权人。
尽管“证据显示,新的去中心化媒介形式正在成为主导,如万维网、移动电话和短信息系统等等。但无论这些新媒体有多大离心的潜力,它们时刻都可能被关于中心的迷思收编”,也因此,库尔德里认为关于媒介化中心的迷思围绕着最根本最重要的资源(符号资源),符号权力集中在媒介手中,但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又被掩盖以致自然化。这最难被解构,所以解构他们的意义就很重大。
从媒介事件到媒介仪式 #
不管是《媒介事件》还是《媒介仪式》,它们都基于一个最传统的涂尔干仪式观:仪式能够实现社会整合,能够维持社会的团结。正如卡茨和戴扬写道的,“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仪式中心,而每个核细胞则通过中心与所有其他细胞联结在一起。就这样,社会最高秩序的统一通过大众传播得以实现。在这个并非常有的间歇时期,社会正处于大众—社会理论家曾经想象的一种既分裂又整合的状态。”
如果说卡茨和戴扬的“媒介事件”还停留在“仪式”上,那么库尔德里的“媒介仪式”就早已把“仪式”解构,并走得更远。卡茨和戴扬的“媒介事件”保持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巩固了现存的社会系统,而库尔德里则在“媒介仪式”中挑破这个社会秩序到底是什么,告诉我们维持秩序的代价可能是让符号资源牢牢掌控在媒介的手中。
从宗教仪式到媒介事件,从媒介事件到媒介仪式,仪式逐渐在传播学者的笔下成了仪式作用的代名词,对仪式的研究本身映射出的也是哲学思潮的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