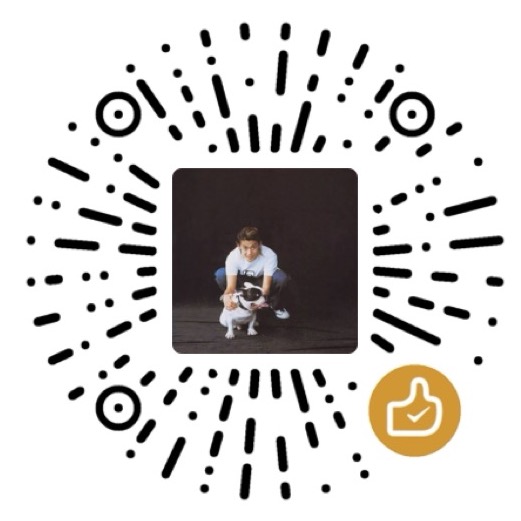听障青少年如何使用媒介
研究缘起 #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和两个同学申请了学校的创新项目,关于听障青少年的媒介使用。我之所以想去研究这个主题,源于本科时期的笔记本。笔记本的某一页,我写了三个关键词:哑语、肢体语言传播、少数派受众。
肢体动作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是重要的传播方式,而主流传播学更侧重研究语言符号,缺少对这类传播方式的关注。同时,我也对“少数派”抱有好奇,他们被“大众传播”遮蔽,但是又亟需发出声音。在我的想象里,传播面向的是最广大的人群,这些少数派既被传播实践活动边缘化,也被传播学研究边缘化。被忽视的部分,往往也是需要被关注的部分。
研究对象是听障,而不是视障,是青少年,而不是老年,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研究便利。选择青少年而不是老年,因为我们的研究方案是想要在某个残障学校做问卷,而走出学校、走入社会的其他年龄段群体,都过于分散,寻找他们要比寻找青少年困难。
不同于视障人群主要依靠触觉、听觉和嗅觉获取信息,听障人群更倾向视觉(人类 80% 的信息获取依靠视觉),所以报纸、电视、手机等都能成为他们的媒介,这使得媒介使用研究的范围不那么狭窄。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对视障人群做问卷调查,需要一个个去“口述问题”,否则就要去设置盲文问卷,这就增大了研究难度。
“无声”的深度访谈 #
由于样本学校高三学生已经毕业,我们对初一至高二的 128 名同学进行了问卷调查。现在看来,这个问卷有很多问题,它获取的信息过于表面。虽然我们算是量化研究,但是没有提出假设(只有问题),因此问题设置中没有考虑变量和相关关系。最终,得到的结果也显得很“不专业”。
调查问卷得出,手机是听障青少年主要使用的沟通交流工具,而报刊的使用率最低,这和整个媒介环境的大趋势是吻合的。问卷还得出了听障青少年关注哪些信息,媒介使用目的和影响等方面的结果,同样和普通青少年类似。
这种“吻合”或“类似”让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最初想法,我以为的听障青少年媒介使用的“特殊性”在哪儿呢?或许这都是我的想象?是我预先把他们看作是“少数派”,看作是不一样的人群,而实际上他们和我们一样,我预先设立的“区隔”是我的刻板印象吗?
这个困惑,通过问卷调查是难以解答的。我们还进行了几场深度访谈。深度访谈是重要的社科研究方法,通常情况下,和受访者面对面交流,企图在表面的问卷调查下获取深层次的内容。和聋人的对话是沉默的,我们通过手写文字来交流,这样的深度访谈是“无声”的。
看不懂的手语翻译 #
通过深度访谈得到的信息比问卷更丰富,也更出乎意料。我发现电视节目上的“手语节目”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现在越来越多录播的电视节目都设置了字幕,一方面是为了照顾人们的习惯,我们的中文“阅读”能力要比“听力”强太多;另一方面也是信息无障碍政策(无障碍传播)的一个要求,可以兼顾听障人群的电视观看。
但是,在电视新闻节目中,有时出现的手语播报员,两个受访女生都告诉我,她们看不懂播报员的手语。“手语翻译用的手语和我们用的不一样,大部分看不懂,我们一般不用标准手语。”“我们看不懂,因为电视上的手语翻译老师是健听人,我们有时看懂,有时看不懂。”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都不是标准手语,而是自然手语。
这体现出一种对听障群体的不理解,尽管在作出改善的努力,但并没有起到实际的效果。有学者提出“自己人效应”,呼吁这些节目应该使用听障人士,一方面能够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另一方面也能了解他们自己需要什么,让手语翻译的设置真正发挥作用。
微信“语音”的另一面 #
在和一位受访者接触过程中,我发现他的手机没有铃声,只有振动,他和朋友需要紧急联系时,打开了视频通话功能,然后两人用手语交流。手机的“振动”功能对健听人而言,提供了响铃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也许只是上课、会议或者睡眠时候的一种“免打扰”模式。
但对于听障青少年(人群),“振动”就是全部。他们依靠“振动”获取信号,因此,手机的语音性服务也是多余的,“振动”是一种提醒,其次还有“闪烁”,或通过短信文字,通过这些提示,他们可以约出对方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可以想象,在手机还没有视频通话功能的时候,它也只是被听障人群作为一种短信收发工具,而不是一种语音聊天工具。
那么现在人人都在使用的微信呢?它最初推出时的主打功能就是“语音”的对话。从听障人群的角度来看,这个主打功能在本质上就是将他们排除在交流环境之外的。也因此,尽管听障青少年也使用微信,但他们的使用方式却是“特殊的”:一是使用打字功能,二是打开视频功能,两个人再通过手语交流。此外,微信的语音转化成文字的功能,对于健听人而言,是为了方便,而对于听障人群,这个功能可以辅助他们“看到”语音信息。
我知道无法使用“语音”功能,不能怪罪到技术工具上,这是听障人群自身的局限。听障人群可以不使用微信的语音功能,但在进入更大的信息圈后,问题就出现了。一旦他们进入到健听人占多数的微信群,交流就遇到了阻碍。一个受访女生告诉我,“很多人为了方便,就用语音讲话;群里开直播视频,也是用嘴讲话的。”当然存在尊重他们使用习惯的情况,但更多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便利——就像我在访谈时,脱口说出问题——而忘记了我们的交流对象。
写在最后 #
正如我在前文中的想象,预设了我们和他们的不同,但这种基于浅层次的捕捉而作的判断,是非常脆弱的。反而是去与他们对话,观察他们的行为,聆听他们的心声,才能去深入了解。听障青少年的媒介使用,或者说我们所有人的媒介使用,概括来看大体都是相同的,这种相同也许是由于人类的本性和共同的社会环境,但仔细去观察,又都不一样,都是与自身进行不断调试的结果。
也许这就是我想要获得的所谓的“特殊性”,一种交流工具想要普及到更多的人,却又总是不可避免地忽视一部分人。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实验叫做“图灵测试”,一端是人,另一端是机器。我们日益依赖微信进行中介化的交流,似乎也正在不断重复着“刻板印象”的测试。在人际传播过程中,听障青少年主要依靠面对面的手语交流。新媒介技术提供了更多样的交流方式,借助微信等社交工具,他们进入更大的社交圈,用一种匿名的形象与更多人交流。
这种远距离的通信带来了外在身份的剥离和内在缺陷的填补,我们难以去分辨对面发来信息的是健听人还是听障人,也就摘下了有色眼镜,他们就是我们。但这依然难以抹平听障青少年和健听人之间的信息鸿沟,其最根本的形成原因在于听力缺损直接导致了在信息获取上被迫失去“声音”信息,只能依靠“视觉”信息,可以说是输在了信息获取的起跑线上。这是对文明的高度提出要求,也是对生理极限和技术难题发起挑战。
然而,回看这项研究,会发现它需要更多对日常情境的观察,以及更多个体及社会变量的引入,只有这样,研究的纬度才会更加丰富,对这一群体的理解才会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