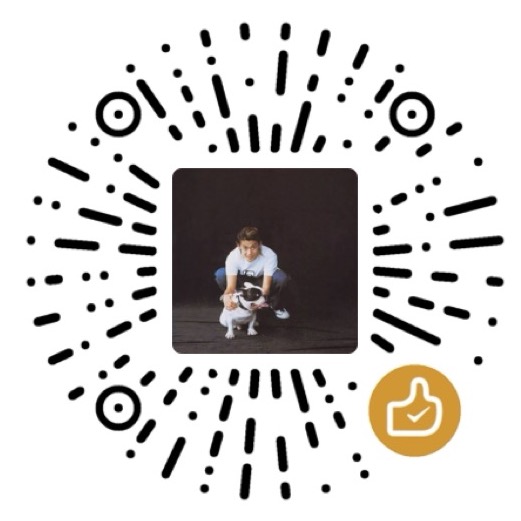Es muss sein? Es muss sein
年轻的生命总是充满困惑,爱情、生死、自我或者彼岸都像是沉默的石块,捡起来扔出去,在水面激起一层层的波纹,随即沉落到湖底。一桩桩心事比这还要重。今天我想书写我的困惑,那种一生只有一次,怎么过才是对的,为什么我是错的。这样的困惑。
纠结了好几个月,我还是在工作和读博上拿不定主意。我知道我热爱读书,但读博后的阅读既是乐趣又成了任务。问题意识最终需要转化成条理清晰的文章,还需要无数的表格、会议和项目。当然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轻松。最近流行的第一次九零后开始谢顶,对我而言也像是戏谑,我也只是拿它开玩笑,并不真的因此而畏惧。那么真正阻碍我去决定的是什么呢?思前想后,我觉得还是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换言之,就是想试试另一种生命路线会是如何。一直在学校呆着,清闲散漫的高等游民生活,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开头的那些困惑,但也困于书桌之前,体会不到真实的经验。那么工作又怎样呢?我看到太多人抱怨老板、职场、加班和年会,也知道这样的选择自带压力,但我也许就是因为没有去体会过,所以才那么想要去尝试。身边很多同学都觉得我适合去读博,导师和父母也希望我继续,包括豆瓣认识的学长学姐也都看好我,但我总觉得我自己不是那么完全地说服自己。就像是我还有其他的选择,并不非此不可。所以我现在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我要去实习,不喜欢了我准备考博。这样的安慰本质上就是一种缓兵之计,真正的选择似乎不是一瞬间的事情,它是漫长的、折磨的,日夜纠缠着。
研究生已经过去一年了,这学期以来能够明显感觉到任务变得密集且复杂,虽然一周只有四门课,但是却要花费更多经历去准备课堂展示。一次是公共传播与政治传播,另一次是城市传播与智慧城市,这两个课题我都很认真的去准备,所以自己收获很多,也得到了老师的表扬。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进步,思路开始变得清晰,前期的阅读积累也开始派上用场。所以我觉得搞研究并不是非要去一以贯之的做学术,而是在一种思维训练,培养的是分析问题的维度和层次。截止到目前,前面的很多任务我都差不多结束了,给导师写了篇论文、随便找了普刊发了创新项目的论文、又交了院里论坛的文章、翻译完研究方法课的英文文献,这几天在准备开题报告的表格。上周四,我去帮妈妈处理一些事情,在公车上坐着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并没有在浪费时间。此前我都觉得既然还在读书,就该好好读书,这些杂事都有些不务正业。但那一刻,我体会到了可以称之为“喘息”的欢悦,尽管它同样复杂,和工作人员的交流就像是两个人互相说着不同的语言,费劲又难中要害。但是它是生活化的,表面浅层的直接感受。这正是我缺少的。因为有足够的空闲才让人有了困惑的可能,忙碌的生活只会让人闷头向前。那些困惑是书本上无解的谜题,懂得答案的人甚至不知道这些谜面。
今天晚上我们年级开会,三十几个人坐在一间小教研室。关于入D积极分子的事情,此前已经在微信群里发了表格,不限制人数所以都可以填表。我之前也上过课,还有结业证书,当然也可以填表。进教室以后,发现大家都填了,只有我自己没有。填表的人轮流发言,我们形式主义地举手表示同意。等叫到我名字的时候,我说我没填表。不知道谁起的头,突然给我鼓掌了。我知道这种掌声里并没有太多的喝彩意味,那一刻的群体压力像是乌黑的云盘旋在我的头顶。回去的路上,同行的同学说了句“清高”,我心里想我不应该去参加这个会。也许是我太单纯,在我的心里这是一个认同的问题。为了未来的某个利益去追随大众,还是为了此刻我能够自我认同。似乎他们做的是对的选择,我也不知道自己这么做对不对,但我只觉得我对得起自己,相比不同原因的去加入某个群体,我似乎更加纯粹。我给男友说群体压力好大,他说比出柜还大吗。我说这么比的话就还好,不过我的朋友都接受了。他说好朋友会关心你是D员吗。我想不会的。把这些话打出来以后,就像是在照镜子,我获得是一种自我肯定也好,自我麻醉也好,我都觉得没那么别扭了。荣耀因人而异,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我大概是太特立独行了,没那么需要谁人的看法,只希望自己能接受自己,能和自己平和不矛盾的相处,因为肉体的痛苦还可以忍受,精神的自我冲撞才是绝症吧。
还有太多的选择需要去做,太多的困惑需要解决。这篇日记叫做 “Es muss sein? Es muss sein”,这是米兰·昆德拉书中的一句德语,出自贝多芬的乐章,意思是: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