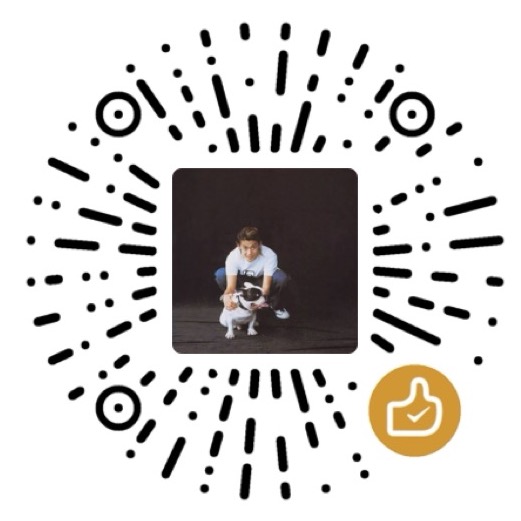城市传播研究笔记
城市与传播 #
城市:定义、历史、经典评价 #
感性认识: 加缪将城市视为现代文明制造的一个空虚世界,而在本雅明的眼中,城市则是一个可以欣赏、梦游、怀旧与陶醉的地方。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中,“所谓城市,指一种新型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世界,它不仅代表了当地的人民,还代表了城市的守护神祗,以及整个井然有序的空间。”
学科定义: 人口学:城市是人口高度聚集的地区,人口规模和密度是判断城市的标准。 地理学:城市是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密集地区,是一种本质上不同于农村的空间聚落。 社会学:城市之所以为城市,主要是城市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城市性。 经济学:城市是工业和服务业经济活动高度聚集的结果,是市场交换的中心。
城市研究:
学科 | 研究对象 | 研究内容
经济地理 | 作为增长机器的城市 | 经济的增长、形态的扩张、大城市、超大都市、城市群、都市圈
建筑规划 | 作为人类容器的城市 | 作为物质形态的空间、建筑、交通等等
人口学 | 作为人口集合体的城市 | 人口流动、群体结构、户籍/社保制度等等
城市人文地理 | 作为空间形态的城市 | 空间结构、住房状况、行政规划、文化产业
社会学 | 城市中的社会 | 农民工、社区、社会分层、公民社会
文化研究 | 作为符号系统的城市 | 符号研究、消费研究、全球资本批判
历史学 | 历史中的城市 | 城市史、城市化史、城市社会史、城市文化史
陈映芳,水内俊雄,邓永成,黄丽玲等:《直面当代城市:问题及方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城市坐落于特定空间并由之所界定。城市是人的生活空间,是以人为主体、以有益于人的体验和解放为价值取向的空间。城市是人们在中介的 ( mediated) 传播中生成的实践空间。
潘忠党:《城市传播研究的探索:“青年的数字生活与都市文化”专题研究的导言》,《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8期。
传播:隐没的空间维度 #
传递信息 VS 建构意义 #
“传播”(communication)是一个现代概念,在14世纪产生时的意思是“聚会的方式”,到了16世纪变成了“被传递的信息”。在这个转变中,传播的重点从肉身在实体空间的“在场”、“相遇”,转向了跨越实体空间的虚拟信息的“传递”。
克琳娜·库蕾:《古希腊的交流》,邓丽丹译,广州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传递”是一个地理和运输方面的隐喻,把信号或讯息从一端传送至另一端。这在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中,被认为是“传播的传递观”。“传递观”主导了主流传播学研究,其研究重点在于“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而经验地事实上”,强调经验研究的真实性。在这个取向中,传播的意义被理解为大众媒介传递信息产生的可验证的客观效果。 而与之对应的则是“传播的仪式观”,詹姆斯·凯瑞“把传播看作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因此,“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
空间:隐没的维度 #
在上面的描绘中,我们会发现主流传播学研究过度跟随“传递观”,同时也过于侧重于大众媒介的研究,而把实体空间排除在媒介之外,这种情形在网络媒体构建出“虚拟空间”后达到了巅峰状态。我们会发现,我们研究的是“云计算”“大数据”,研究的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但我们却忽略了现实中的实实在在的空间,因此,有学者把“空间”称为“隐没的维度”。
但其实我们回顾一些传播学著作,还是能够捕风捉影到一些只言片语,比如:
威尔伯·施拉姆把包括石雕、纪念碑、泰姬陵、金字塔和教堂等在内的建筑物统称为“无声的媒介”:“石雕传播古代诸神的庄严伟大,建筑物和纪念碑传达了王国或统治者的丰功伟绩,泰姬陵和金字塔等名胜古迹、教堂的非凡构想不仅召唤人群、传播生活方式,而且传递民族的历史、讲述其对未来的希望。”
哈罗德·伊尼斯从时空层面,将传播媒介分为两大类:空间的偏向和时间的偏向。前者有莎草纸和纸张等,它们轻巧方便,利于在空间中进行远距离的信息传播;而后者有如石碑和泥板等,它们笨重耐久,不适合运输,承载的信息在时间维度上更持久。
佐藤卓己《现代传媒史》:那么,如果说城市就是媒介,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奇怪?
城市传播研究 #
作为媒介的城市 #
城市的确可以作为一种媒介,甚至可以被当作巨大的媒介“星丛”(吴予敏),“实体空间的媒介作用不但从未在都市文明中缺席,甚至不断在彰显。空间作为媒介,它的嵌入日常生活场景的具象表现方式,与地方化集体记忆的历史连接,等等,都使得它的传播内涵与意义独树一帜。”
孙玮:《作为媒介的外滩:上海现代性的发生与成长》,《新闻大学》2011年第4期。
城市传播倾向于“传播的仪式观”,它“不是指空间上讯息的拓展,而是指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城市与传播之间的关系,是意义的生成与互动的展开,在城市中,文化意义得以创造与共享,新型互动关系得以塑造与展开。作为媒介的城市,是以空间为研究进路的。城市中的建筑、交通、自然环境等等,都对创造城市意义、生成城市文化产生影响。
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城市通过它的许多储存设施(建筑物、保管库、档案、纪念性建筑、石碑、书籍),能够把它复杂的文化一代一代地往下传,因为它不但集中了传递和扩大这一遗产所需的物质手段,而且也集中了人的智慧和力量。这一点一直是城市给我们的最大的贡献。
浙江传媒学院崔波老师的《城市传播:空间化的进路》,主要思路是城市传播的“泛媒介”视角,物质空间传达出城市意义,塑造城市形象带来城市想象,她写道:
城市中物质性的空间不仅仅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和社会性的呈现,还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结构体。它们既以自身的真实实体而存在,又赋予城市一种想象性的现实。”
但遗憾的是,这本书后面的内容却不依照这种“空间”进路做研究,而有些大杂烩。
相关论文: 1. 孙玮:《作为媒介的外滩:上海现代性的发生与成长》,《新闻大学》2011年第4期。 2. 孙玮:《 “上海再造”: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城市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3. 陈霖:《城市认同叙事的展演空间:以苏州博物馆新馆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8期。
媒介对城市的呈现与塑造 #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方玲玲的《媒介空间论:媒介的空间想象力与城市景观》中,通过媒介地理学来切入城市传播,她认为:媒介地理学中的“媒介”概念,可以理解为麦克卢汉所指的包括道路在内的广义媒介,也可以专指各种传媒。这两种意义上的媒介都可以与社会文化、地理空间相连,建构出丰富的文化地理样貌。
因此,虽然这么书叫做“空间论”,但其主要内容却着重于大众媒介,她写道“大众媒介能够通过多样的方式,来阐释城市的文化与精神层面”。她分析了书籍、报刊、电影、电视等媒介对城市形象或城市文化的呈现与呈现;其次,基于晚近地理学的研究走向,还分析了城市空间与性别、种族、性取向、亚文化等的结合。
延续着这一思路,媒介如何呈现与塑造一座城市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发现很多。
- 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弥漫着忧伤与“呼愁”(hüzün),这是某种具体而非个人的忧伤。“呼愁”不提供清晰,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的茶壶冒出蒸汽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不是主张个人反抗社会,反倒是表明无意反抗社会价值和习俗,鼓舞我们乐知天命,尊重和谐、一致、谦卑等美德。
- 《纽约客》撰稿人E.B.怀特《这就是纽约》中,“纽约是艺术、商业、体育、宗教、娱乐和金融荟萃之地,在这么一个浓缩的竞技场上,挤满了角斗士、布道者、企业家、演员、证券商和买卖人。”“纽约就像一首诗:它将所有生活、所有民族和种族都压缩在一个小岛上,加上了韵律和内燃机的节奏。”
- 野生摄影师刘涛的正经职业是抄水表工,业余摄影,他的镜头之下,“合肥”显得光怪陆离。
- 《北京遇上西雅图》中汤唯的面签通过,她的理由是《西雅图夜未眠》,我们能在这部电影里看到电影呈现城市后,对人的影响。为什么是西雅图呢?电影让这座因为常年降雨而寒气逼人的城市,充满了浪漫的暖意。
城市传播的互动关系 #
城市传播的研究对象是,作为媒介的城市以及城市中的传播。
孙玮:《 “上海再造”: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城市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日本学者佐藤卓己在《现代传播史》中将城市视为媒介,他将媒介定义为“具有沟通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功能”的工具,在这个预设下,城市被视为媒介——一种由于经验而产生关联的场所。关联或关系成为城市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王安中和夏一波的《C时代:城市传播方略》,从传者、内容、受众、渠道角度系统分析了城市传播的关键要素,并且考察“城市与乡村”、“旧城与新城”、“全球城市与本土”等的互动关系。
关系既有实体网络构成的,比如街道、公路、铁路;也有依靠虚拟网络加以支持,比如报纸、电视、互联网。这种网络的实质都是在缔造一种传播状态——信息传递、社会交往、意义共享——以建立一种关系。比如,城市地标性的区域与建筑物,不仅是实体网络的重要节点,也作为城市的精神象征,塑造城市认同,沉淀城市记忆,具有丰富文化意涵;而虚拟网络的影响则常常以具体场景中的现实行动加以体现,大众媒介的信息传递常常引发或转化为实体空间的实践。城市的传播就是编织关系网络。
黄旦主编:《城市传播:基于中国城市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这种观点强调现代城市空间的体验是融合性的,建筑物、物质空间、传播媒介、社会实践共同构筑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传播、交往、沟通的过程。如果说,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盛行时代,媒介常常被视为“再现”城市现象的“中介”,那么在无限移动的新媒体时代,大众媒介和城市空间已经彼此融合,难以分割,它们共同构筑了城市传播的整体。
相关论文: 谢静:《连接城乡:作为中介的城市传播》,《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马中红:《第三种论坛:体制性网络空间的公共性透视——以苏州 “寒山闻钟论坛”为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第8期。 杜丹:《镜像苏州: 市民参与和话语重构——对UGC视频和网友评论的文本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第8期。 於红梅:《数字媒体时代城市文化消费空间及其公共性——以苏州平江路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第8期。
补充:可沟通城市 #
“可沟通城市”是目前城市传播研究的核心概念。
“可沟通城市”概念来自美国传播学者倡导的communicative city,最早由哈姆林克(C.Hamelink)在2007年夏的一次学术交流中提出,他把“可沟通城市”看作是基本人权的体现。冈伯特和德鲁克(G.Gumpert&S.J.Drucker) 把“可沟通城市”的特征概括为三方面:首先,城市居民的日常传播活动及其沟通模式应该提供交往空间或者机会,让市民进行各种社会交往和互动;其次,城市的基础设施应该鼓励城市中顺畅的传播;最后,城市应当创造鼓励自由政治表达和公民参与的环境。 谢静:《可沟通城市:网络社会的新城市主张》,《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7期。
提出的背景是:城市市异质性特点导致的“失序”状态,是城市危机最主要的根源,“陌生人”的混杂是“失序”的原因,构成了对大城市的威胁。孙玮认为“可沟通城市”是城市传播的核心概念,将城市理解为一种关系性空间。 孙玮:《城市传播:重建传播与人的关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7期。
“可沟通城市”一词所关注的正是当今城市的可沟通性问题,或者从本质上说,是如何通过理性化的沟通过程重建社会共同体意识的问题。
吴予敏:《从“媒介化都市生存”到“可沟通的城市”——关于城市传播研究及其公共性问题的思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3期。
参考文献
-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 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 崔波:《城市传播:空间化的进路》,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 方玲玲:《媒介空间论:媒介的空间想象力与城市景观》,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 黄旦主编:《城市传播:基于中国城市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