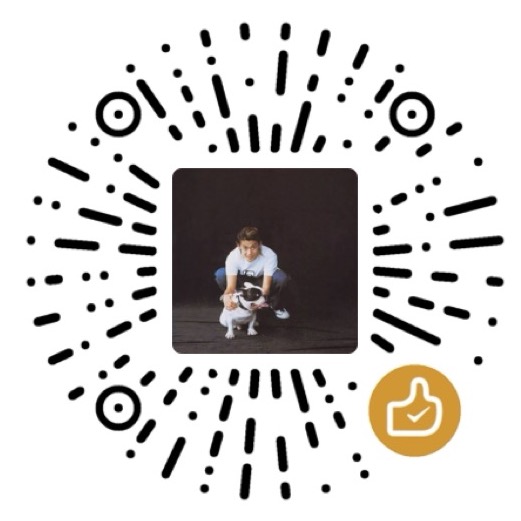巴别塔与巴别塔毁灭之后
我之前洋洋自得地写过这样一段话:
传播的终极目的是对话,通过对话来抵消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隔阂和冲突。对话本身就区别于灌输和宣传,权力意味没那么浓。如果要幻想传播学的学术愿景和乌托邦,那应该是一个人人可以自由交流、平等对话、相互理解的世界。
看彼得斯的《对空言说》1,才意识到“对话”之论的缺陷也如此之多。在最原本的意义上,对话是少数人间面对面的具体交流,口头语言和表情动作一起承担着思想的传达工作,但对话为交流设立的标准又太高,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内,对话要求对话者自由平等理性批判,此外对话还要求回应,这种回应近乎“强迫”。而当前,我们对“对话”的一致推崇实际上已经构成了霸权般的规范,作为交流的工具,它并非是至高无上的唯一。
因此,彼得斯在“对话”外提及“撒播”,它们构成了本书的一对重要概念。
彼得斯将对话追溯到柏拉图的《斐德罗篇》,其中描述了苏格拉底与斐德罗的故事,苏格拉底还演讲了自己对对话和文字的看法,他认为口头的对话是具体的互动,而文字没有人性,缺乏亲切感,忽视听者的个性。这种担忧一直持续到我们对大众传播的看法,在文字之后,我们担忧广播和电视。
而撒播的意象则来自圣经福音中的“播种者寓言”,其关键是“凡有耳者,皆可听,让他们听吧”。“撒播”成为一种公平公正的交流形式,它将意义的收获交给接受者的意愿和能力。这就意味在撒播的时候,更关注内容,而非接受者的回应,这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爱”。因此,彼得斯说:“单向的撒播应该是我们更加冷静的根本选择。”
然而,无论是对话还是撒播,都难以弥合交流中的沟沟壑壑。我们需要交流(不管是对话还是撒播),正是因为我们在交流中的无能为力,那些难以消除的误解,那些不被听到的声音,“我们渴望交流,这说明我们痛感社会关系的萧条荒芜”。
彼得斯笔下,交流呈现出两个方向:“传心术”和“唯我论”,这也是交流的两个极端。前者有天使学的影子,作为上帝的信使,它能实现灵与肉、神与人的对接,“传心术”就是思想的无障碍共享,是人与人之间“瞬间可达”的交流美梦;后者则认为“个体是意义的主人”,“自我”是交流的阻碍,我们的思想在脱口而出时已发生变形,在记录成文时便成为无主幽魂,人们像是被困在封闭的房间,威廉·詹姆斯写道,“这样的思想之间的割裂,是自然界中最绝对的割裂。”
我联想到了巴别塔。在《圣经·创世记》中,关于巴别塔有如下记录: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巴别塔构成了一种交流的隐喻,“传心术”和“唯我论”就像是描绘了巴别塔与巴别塔毁灭之后的两个世界,第一个世界人们言语相通,交流的力量非常强大,而在第二个世界里,即巴别塔毁灭之后,交流成为一种不可能。
不管是“传心术”还是“唯我论”,极端性都让它们难以轻松立足。但纵观人类的历史,我们都竭力逃离“唯我论”迷宫般的噩梦,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各种中介来实现彼此的联通,向着“传心术”迈进。也因此,每当新的媒介技术出现,人们都要感叹美梦成真,但也用不了多久,我们再次向交流之无奈低头。
先是让口语保存成文字,以为思想记录在案可以穿越时空,但在苏格拉底看来,作者的缺席让文本失去指向,成为滥交的撒播。后来,又用留声机抗衡随着时间一并消逝的声音,它同样具有两种特征:忠诚(对原声一成不变,忠实记录)和滥交(对听众不分对象,滥交撒播)。电话开始实现远距离的通讯,一对一的交流有时候却成为了相互交叠的独白。无线电广播也摆脱不了对大众传播的习惯性批判,即使它模仿对话场景,让人倍感亲切,让人以为“这是特别说给你听的话,而它实际上是说给所有人听的话”。
这让我想起《Sense 8》里的“传心术”和思想的接触,有人评价说主角们实现了人类“最大限度的不孤独”;想起王菲在《打错了》里的歌唱,电话让交流成为两段彼此隔离的独白;想起电影《HER》里,人机交流的虚伪性。一个机器对着你说话,但实际上她也对着所有人这么说,我们对人机交流的渴望,其实就是对思想接触的渴望,对“传心术”的渴望,对一个更懂自己的“哲学之爱”的渴望,但是电影中恋情的失败显然在告诉我们,依托于媒介的交流,也被媒介所阻碍。
在“死信”的篇章里,彼得斯写下这样一段话,它很长甚至“老调重弹”,但足够引发深思。
永远无法送达的信——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说明交流误入歧途之后使人扼腕的哀怨呢?我妻子在脑子里哼的曲子、我醒来时忘掉的梦境、小孩子独自与自己的玩偶进行的聊天、我躺在枕头上时耳中听到的自己的心跳、深埋在冰川表面一英里以下的猛犸象肉的气味、日本神风飞行员衣袋中的家信;对奥德修斯船舱中的船工和士兵来说,女妖都对他们唱了些什么?处于紫红色与红色之间的颜色是什么样子的?牙医给牙病患者施加麻醉后实施手术时,患者的牙周神经有何感觉?有哪些伟大的作品被埋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事物内部的颜色、湿度和温度如何?对所有这一切问题,我们都容易一笑置之,嘲笑这又是在老调重弹那个过时的难解之谜——“密林中一棵树倒下,若无人听见,那么树倒声还真存在吗?”但是,我却不觉得是在老调重弹。“死信处”的信化为灰烬,而发信人却不知道信已丢失,收信人又不知道信是否真寄出了。你说那被烧掉的信,其意义何在呢?
意义何在呢?它们是我们存在的鬼魂,被放弃也被捕捉,是我们交流的渴望和失败,悲哀而神圣。
[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