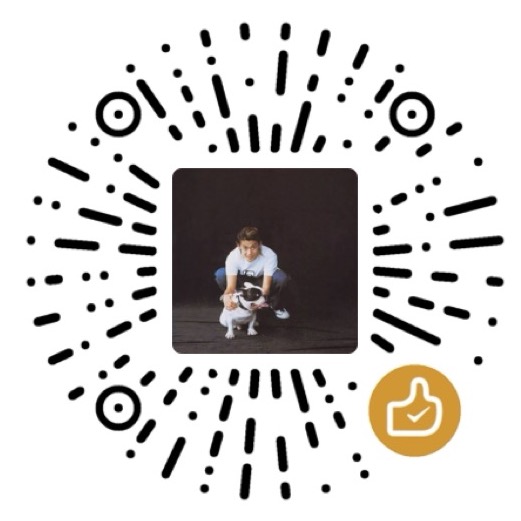卢德分子
冯尼古特在《没有国家的人》中,称自己是一个“卢德分子”Luddite,仇视新奇发明的人。
据传,内德·卢德是十九世纪初的英国纺织工人,由于当时机器取代人力,熟练工的技能贬值,他十分痛恶,因此怒砸机器纺布机。卢德运动就此展开,这一运动始于1811年的诺丁汉,后迅速蔓延至英格兰。卢德分子们摧毁了许多羊毛和棉花工厂,甚至还集结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与英国陆军对抗。
在当时的英国,捣毁机器被定为重大罪行。这项法案遭到了拜伦的反对,他是为数不多的为卢德分子辩护的知名人士,甚至还写了一首名为《Song for the Luddites》的诗歌。但拜伦的反对显然是徒劳的,1813年一场于约克发生的暴动被镇压后,十七名参与者被判处绞刑,更多人被流放到澳大利亚。
这就是关于卢德的故事,在这里,我并不想谈论机器如何改变就业状况,人工智能如何使人们更懒。我想说的是,当今时代,仇视新奇发明也许并不会导致流放和绞刑,但那些卢德分子却正在经历另一种形式的驱逐。
在传播学界,有一位著名的卢德分子,不同之处在于他写书批判,而不是去砸坏电视机。他就是尼尔·波兹曼。不管是在《娱乐至死》还是《童年的消逝》中,他都旁征博引声嘶力竭的证明电视机毁坏了人们的生活。他认为,印刷时代属于阐释时代,逻辑理性、冷静客观借印刷术发扬,人们沉浸在严肃的阅读氛围中,而电视导致了娱乐业时代的到来,信息虽然井喷,但质量却差于阅读。
这种保守主义的态度自然会被技术崇拜者所鄙夷,就像是当人们早已不再拥有过去的记忆,在人造乐园里整日嬉游时,有人提醒他们要记住乡愁,寻回昨日的世界。放开想象,尼尔·波兹曼如果见证了互联网的蓬勃和人工智能的兴起,他又会如何感慨。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把卢德分子称为“活在过去的老顽固”,他们也许还在用着老式的收音机、笨重的旧电视,不能上网的手机,手写信件,而不像潮流人士收听网络播客,看曲屏超清电视,使用阅读器、智能手机和电子邮箱。但他们明显不被商人和消费环境所鼓励,他们可能在自动售票机前纠结好久,以至于身后排队的人连声抱怨,还可能对着一个全自动洗衣机发愁,不知道每一个按钮的意义。
上世纪的预言家在书中的预言逐一实现,混淆了预言的世界和目标的世界,这些当代卢德分子所遭受的驱逐看似是自己无法同步适应技术的变化造成的,但也有人质疑技术变化的是否过于迅速和无常,以至于无暇顾及使用它们的人。在现代生活中,我们所依靠的东西已经离传统越来越远,而进步的方向也总是被变化牵着鼻子。
冯尼古特的妻子在他出门前质问他,为什么不多买一些信封放下家里,非要去邮局。或者我们也可以自问,为什么我们越来越懒,不去商场而是依靠网商依靠快递,为什么我们的兴奋不是来自于在路上发生的一切,而是收到快递已经到达楼下的信息。
冯尼古特没有回答他的妻子,而是用他的行动解开了谜底。他喜欢偷看邮局的女员工,喜欢用舌头舔信封的胶,喜欢看信件的称重,喜欢把信件投进邮箱。他觉得,电子的世界里什么都不会发生,只有当一个人去与生活正面接触、碰撞或磨合,他的生活才会更加有趣。
这么想着,我大概也是一个卢德分子。
本文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24期(总9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