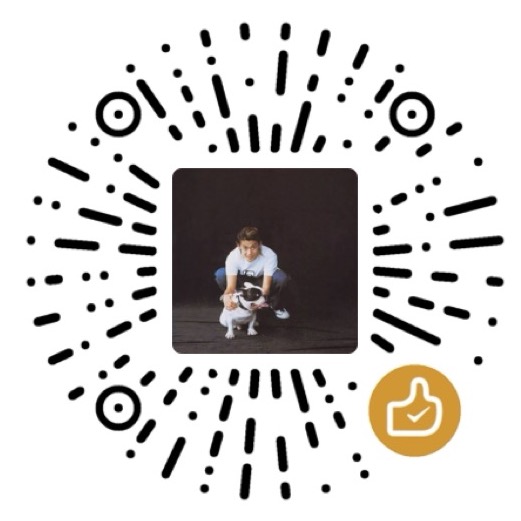河马
快 #
哈扎尔辞典里提到,熟睡的时候乃是一个人最为脆弱之际。所以每夜临睡前,阿捷赫公主都命令盲人在她的两片眼睑上书写诅咒的字母,凡是看到的皆难逃一死。然而颇为讽刺的是,阿捷赫公主却死于清醒时刻。字母的力量的确守护住了她的睡眠与安全,但某个早晨,她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那是一对镜子:快镜和慢镜,顾名思义,前者预示未来,后者重现过去。于是,辞典里这么写道:
她是在来自过去和来自未来的字母的同时打击之下与世长辞的。
辞典里没有提及把那对魔镜放在公主床边的奴婢有何下场,也没有说明那些书写诅咒字母的盲人作何处理,这些一直都是历史或者所有叙事的暗角,由于它需要主人公,需要道具,需要强有力的故事,因此无法面面俱到,没完没了。此类的暗角还出现在帝王陵墓的匠工身上,他们的存在甚至还不如砌石强硬;出现在千金小姐梳洗的铜镜里,生活一如映像般脆弱飘摇;或者还出现在降生便被注定为人侍奉的仆从身上,但并不是每一个都忠诚如桑丘;出现在英勇将士披斩的钢刀里,命运一如血刃般冷淡寒切。
正是由于每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去看待整个外部环境,成为传记的撰述人,所以暗角无处不在,它就是我们不可体谅的他者,我们视野之外的无知,甚至还包括我们身体之内未被发觉的秘密。为了更好地理解暗角,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不是去寻找暗角的踪迹,而是抛开主人公的身份,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稍不留神便会被遗忘的暗角。
当我们成为暗角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只能成为自身的记忆,成长的历史不过是写在本子上的只言片语,或者是刻在心里逐渐被磨平的伤痕,散落如砾,难融于世。在某些时刻我们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众多孤儿中的一个,但更讽刺的情况可能是在降临之前我们已经被迫离开。我不能在这里列举出太多细枝末节的悲伤或欣悦,因为几乎所有的一切并不单纯指向生命的终结,而是它们总是不被在乎、不被了解,以至于我们以为自己拥有了独特,但其实只是拥有了和万千陌生人一样的体验。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想象力还支撑不住暗角的阴翳,所以我们会选择性地忽视它,就像是我们也曾被选择性地忽视。但想象暗角并不仅仅是为了怜哀自身,那会是一份傲慢的怜哀,当然也不仅仅是为了同情他人,那同样会是一份傲慢的同情,它的目的就像是在迷雾中一步步拓开可视的范围,理解已知的同时又去探索无知,最终这种想象将变成一种怀疑,而当怀疑的风越刮越紧,过往坚定的堆积物总归是要化解成沙。
是否存在一种极力摆脱暗角的个人命运?方野放下酒杯,摘了墨镜,擦了擦鼻梁上的细汗,对面的男人这才看到他的眼睛,空然如夜。作为一个盲人,我能感受到暗角的力量,但作为一个诗人,我知道我会被书写在典籍之中为后人评说。他重新戴上墨镜,对男人微笑。原来,故事讲到这里只是刚刚开始。
慢 #
你尝试过闭着眼睛行走吗?方野的问题似乎永远不需要答案,他抛出一个问题,紧接着便会继续言说。即使是在空无一物的广场,闭着眼睛所带来的也会是安全感的丧失,而黑暗的恐惧就借此快速蔓延。但睡眠却不同。同样是闭着眼睛,它却只被视为死亡的练习,即睡眠的黑暗恐惧并不致命,或许这就是阿捷赫公主死于清醒时刻的原因,也是行走比睡眠更危险的原因。这么说来,我就不经意地反驳了辞典里的睡眠脆弱之说。可以发现当你感受到危险,第一反应会是僵停,担心任何冒进都会带来未知的痛击,这不正表明你认为静止比行动更加安全。
我便是如此。清醒时刻的每一个举动,都像是在和黑暗的恐惧搏斗,反而是停留让我感到安心。搏斗的最初我始终是输,后来认清了恐惧的面目——是的,即使看不见也能认清——我才懂得如何与之搏斗,我的武器从父亲的手掌换成了木杖,我的盾牌从母亲的怀抱换成了皮肉,慢慢地放招,慢慢地平局,慢慢地赢。仿若每次搏斗都以诗下注,无论结果,诗也慢慢地跟随,时多时少。但诗的语言却从丰盛走向贫瘠,现在我才明白那是我对世界模样的记忆正不断瓦解。
少年时期我领会过世界的曼妙多姿,记忆里天空泛蓝,林野发绿,旧街的石墩被磨出银灰,穿城的河流被送给黄昏,层层叠叠的色彩仿若是光的幻术,但一切还是逃不出魔鬼的一击。方野的语气里带着旅人回不去的遗憾和乡愁,他说,我已经习惯了现在的晦暗,十八年过去,它刚好长大成年,其后的路依旧如昨日茫然无期,但拒绝它也就是在拒绝自己。只是曾以为能够为记忆做出注脚的诗,却在背叛。
当它不再吟唱尘世,只专注于深处的秘密,它就从歌颂走向忏悔。我给女友写信,却又不寄。信里我一边诉说着不忠,一边为自己开脱,甚至在告诉她我多么迷恋另一个女人的身体后,又不知羞耻地乞求原谅。我称赞她的洞察力,在发现了我藏在大衣口袋里的猫腻后,及时结束了我们的关系,我称赞她的果决,在结束后我日夜想念,她却没再与我相遇。——也许,她总能躲过我的眼睛。
我又给男友写信,依然不寄。信里我分析失败的主因。我们曾对感情抱着放任态度,以为各自行事,留出的空间也会浪漫的花草丛生。但其实,我们越是自在,我们的关系越是疏离,最后我们之间寸草不生,那片空间成为了情感的荒漠。本来深爱的两个人,就这样在情感里迷失,甚至察觉不到荒漠的危险,也不再去相互依靠,就这样被彼此放逐。但为了让他得到解救,我在信的末尾对他撒谎,是我又错爱了别人。
我还给父母写信,同样不寄。信里我伪装出一副幸福的模样,希望他们在天国为我祝福。写着写着我意识到欺骗亡者最为愚蠢,因为我们相信神无所不知,那么祂的信徒也当目睹一切,所以我转而叙述一段段看见和看不见的旧事,寄托沉重的思念,把泪洒在手背上,小心不让它们沾染我笔下的俗气。是时候让他们放心,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位盲诗人,虽然难达远古荷马的高度,但已被许多人传诵,他们也不再是卑微的暗角,而会作为诗人的父母被书写在传记的开篇。
和许多人一样,你坐在我的对面,称赞我的才华复又称赞我的长相,就像是我手握明镜,自在地承认它的虚伪。对面的男人表情诧异,只听方野继续说,诗已经在背叛我,接下来将会是你们,语言永远都不会可靠,因为是语言教会了我欺骗,而你们教会了我去相信那些鬼话。方野对男人说,我要喝酒,陪我喝酒。
镜子 #
对面的男人费劲地拽起倒地的方野,一只手环过他的腰紧紧抱住,腾出另一只手去拦出租车。但经过的司机透漏着厌恶的神情,就像是方野的呓语,始终不愿停下。方野挥动着木杖,于是夜就成了一尊无边无形的巨兽,两个人站在它的身前,不知何处是它的脚跟。突然,木杖悬停在半空中,随即一辆车停了下来,像是被拯救但更像是两个逃兵,他们扎进了车里。电台里正在放送音乐节目,女播音员念完听众留言后,一曲《路口》盈满车厢。等她再次念起留言时,男人拖着方野下车。他抬头看了看,一扇黑窗正悬在顶楼。
他决定等方野稍微酒醒后再上楼,至少这样既安全又省力,于是两个人坐在路边的木椅上。方野半醉半醒地说话,男人只是似听非听。他不曾读过方野的诗,其实,他并不擅长阅读,在他的家里唯一和阅读相关的或许就是垫在桌子上的旧报纸,虽然文字无处不在,但他从不关心具体的内容。方野的背包正攥在男人的怀里,他打开看了看试图寻找什么。他找到了,那是方野的记事本,他知道那里面有诗,甚至是诗的胎芽。
不只是汉字,本子里还写有英文和日文,他无法想象一个盲人怎样规整地写字,就连标点也用得如此妥帖。首页写着方野的姓名和地址,原来他们正坐在旧街,向南走去便是英雄广场。其后的每一页上都有方野的诗句,再往后就是他提到的几封信。即使到了这种时刻,好奇心驱使着他找出了记事本,也没有成功让他去品味几句诗,他合起本子,然后点燃一根烟。在男人的眼里,方野的诗歌毫无吸引力,唯一的特别之处只是他失明的双眼。方野引之为傲的声名受到男人的冷落,反而是他的暗角在男人的脑中膨胀生大。
男人把方野的墨镜取下戴在了自己脸上,本就黯淡的夜透过这层薄幕显得愈发诡谲,它甚至改变了风的温度和草丛的气味,一闪而过的车也显得神秘非常,他又看向方野,正安静地坐着。把墨镜还给他,男人踩灭烟头,搀起方野示意上楼,等他们打开房门的时候,男人才意识到背包忘在了木椅上。他飞奔下楼,又快速返回,方野歪靠在沙发上,桌上摆着两杯清茶,男人气喘吁吁地坐回他的对面。
感谢你的善良和诚恳,在车站的取票口遇见后一直到现在,你都那么耐心地听我疯言疯语,甚至还好心送醉酒的我回来,我能有今天的运气是多么难得,这世上还有你这样的人多么难得。你或许觉得我过于悲观,但只有你身处在金字塔底才会明白我的情绪,你能看见人们,能看见人们的可笑与慌张,而我的生活却依靠想象。我说过,关于过去的记忆正在瓦解,那是因为这世界变化的速度没有谁能跟紧,我对它的了解只能来自想象。听说英雄广场的雕像已被重塑,但我还停留在他的笨拙与残败,我还听说女歌手含针而亡,而我的印象里她却永远是少女的身姿。
这么说来,我就像是在那天预先得到了终结。我不得不提起那天的事,十五岁的某个傍晚,我和父母在树林里沉默地闲逛。父亲刚刚失业,大概在思考如何继续往后的日子,而母亲又对我失望,只因在学校糟糕的表现。我边走边四下张望,突然一阵晕眩,跌倒在地。等我醒来,黑夜就此降临,那一刻我分不清何处是它的边界,它侵入我的身体此后没再离开。他们都以为是地上的石块造成了这场意外,但其实那天下午我就被施以报复,我只记得棍子打过我的脑门,却不知道是谁。
在我的代表作里,它被称为「魔鬼的一击」。方野把杯子放回桌上,不小心碰到了左边的花瓶,对面的男人及时接住才免于破碎。对,就像是我刚才的碰撞让花瓶倾倒,我的少年时期也在那片树林倾倒,再次起身,我已属于另一个世界,并与之搏斗至今。我的伤痕满身,我的忧愁密布,我的孤独成为杠杆,挑动着无人能够承受的疲惫;我的锋芒微暗,我的言行缓慢,我的忏悔成为新药,治愈着多年未曾恢复的旧疾。
我想睡了,说了太多的话让我感到不安。方野摸索着走进卧室。男人一动不动地坐着,随后他把清茶饮尽,走向窗台抽烟。外面开始下雨,一个年轻女人在对面的窗旁倚着,看见了他就向他问好,他点头致意。年轻女人说,你的眼睛在雨夜里泛着敏锐的光,那么好看为什么总戴着墨镜,为什么人们都迫切需要装扮来掩护真正的心,为什么到了难眠的深夜才想去面对它,为什么我努力了那么久失落的巨石还是压着我不放,为什么我宁可扛起这份不相称的重担也不愿离去,你是诗人请你告诉我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