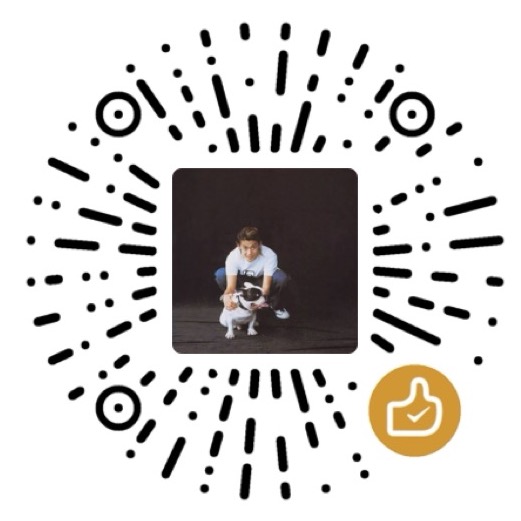乡愁、牧歌和现代生活
寒假期间看《梵高传》,写下批注:似乎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慨叹自己所处时代的庸碌麻木和淡然无味 ,哀悼昔日的辉煌。文明仿佛永远处于“衰退”状态,社会也总在“腐朽”。其实仔细想想,不管是中国历史上,孔子慨叹礼崩乐坏,追回内外一致,历代文人古文运动的“复古情怀”,还是欧洲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美好追忆,“文艺复兴”,乃至当代政治家提出的“伟大复兴”(Great Again),都暗示着我们的过去如此荣耀,现在的处境实在可怜。
读研以来,看的一些书都关于“共同体”这个主题。根据学者们的观点,鲍曼觉得它是失落的天堂,其中充满安全信任,温暖关怀。而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社会的前状态,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传统共同体不断瓦解,陌生的人们走进城市形成社会。很多学者都怀念共同体,相信共同体的重建,可以帮助解决当下的一些危机,比如信任感降低、个人主义至上、信仰丧失导致的虚无感。
这样的憧憬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我。之前看到《历史的终结》里,写道“接受现代教育的人满足于坐在家里,庆幸自己心胸开阔,没有狂热的偏执。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论及现代人说:因此他们说:‘我们是完全真实的,没有信仰和迷信。’于是,你们挺起胸膛——但是,啊,那是空洞的胸膛。”我想,当人们不再为被认为是想象的国家或民族而战,对历史传统一味的拒绝而投身在无根的现代,或者是个人的追求不再与集体相连结,人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共同体确实可以作为一种填补这些空洞胸膛的方式,弥合种种裂痕。
但是今天,我看了《后现代的状态》,里面又这么说:我们将在后面分析这种大叙事的崩溃,按照某些人的分析,这种崩溃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瓦解和社会集体转向一种离散状态的过渡,个体原子被抛入荒谬的布朗运动。其实并非如此。在我们看来,上述的观点似乎是模糊的,因为它把一个失去的“有机”社会描绘成了乐园。
和希望追回古典生活不同,后现代的角度直接怀疑了“复兴”或者“复古”的必要性。因为我们把曾经的生活当作好的,认为那才是“黄金时代”,所以我们才想要重返。但是那样的生活是真的好吗?在怀念过去的好时,我们总会忽略其固有的痼疾,而我们在批判当下的坏时,却又总会忘记它的进步。这么看来,我们的时间观念是存在偏见的。
或许和“重返伊甸”类似,学者们想要重返过去,不过是提炼出曾经的纯真和善美。就像我们用乡愁,把故土怀念成一片绚烂的宝石。这么写着,我意识到学者们其实是看到了当前的困境,为此找到的出路。这才有了两种分歧:关于过去的怀念,和关于未来的向往。在过去,人们较为紧密的生活所孕育的乡愁是美好的;在未来,人们运用智慧达到的乌托邦是值得向往的。但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这样的希冀都属于牧歌。只有现在,永远索然无味,却又在回忆时闪着光。
说完这些,我想来谈谈自己对待这样的问题时的思维变化。年少时,我叛逆又片面的反对着传统,认为那是一种对成长的禁锢;后来逐渐意识到传统的优良成分,并觉得这可以帮助缓解现代社会的病痛。今天,后现代的理论似乎又质疑着这种药剂是否能够对症治愈。这么看来,似乎只能寄希望于未来了,因此人们计划着未来,设想了理想国,让科幻小说和未来学预言逐个成真。这本身就像是一个拔河比赛,不管是往哪个方向用力,被争抢的都会感到疼。而我们就在中间。
我是有必要选择立场的,是向过去靠近一些,继续沉迷于共同体,或者是向未来靠近一些,想象着乌托邦。但我知道回去太艰难,未来又总在意料之外,要想处理现实问题,只好张开双臂握紧绳子,把两端同时拉到自己身边。不过,这也都是说说而已。
本文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27期(总9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