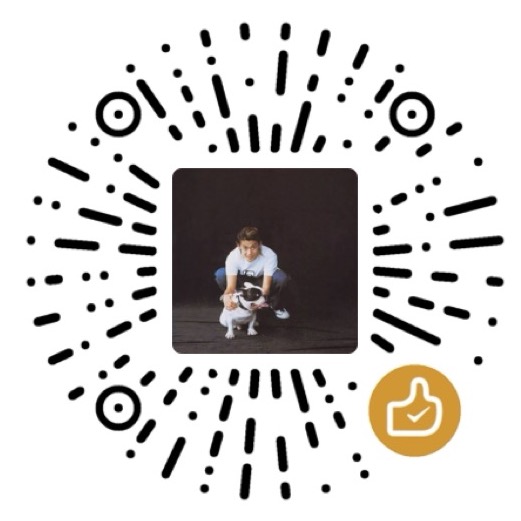潮湿俱乐部
我们离开城市的那个夜晚,空气凝滞,蝉鸣在高温中起伏。我们手拉着手,可以感受到彼此的手汗。在奔跑的间隙,我们回头看,西边的天空一片橘红,湮没了星星和月亮,能隐约听到消防车的声音,偶尔还有尖叫和狗吠。我们带走了必须的财物和一只叫做“舌头”的英国短毛猫。在不必须的东西里,我们带走了地图,尽管我们知道这会暴露我们的行踪,因为有了地图就有了目的地。我们还带走了一顶帐篷,虽然可以睡在车里,但我们打算在某些时刻露营。
我们以每小时八十公里的速度离开城市,不是旅行而是逃亡。这是一个真实故事,故事发生在一个闷热的夏季,为了保护我们的隐私,我们必须隐去名字、性别和年龄。这也是一个公路故事,诗人说过“生活,在别处”,而我们知道“生活,在去往别处的路上”。这还是一个酒神故事,我们要把自己投射在万物之中。狂欢?迷乱?也许不行。我们必须安全地离开,尽管我们并不确定要去哪里。
1 #
我们把舌头放在后座,一开始它因陌生而拘谨,缩成一团睡觉。但随着天空逐渐亮起,舌头似乎也变得活跃了,它尝试从后座往前排跳,我们把它推回去,它又跳我们又推,几个来回以后,它又爬回后座继续睡了。这时候,道路变得坑洼不平,车子颠簸得厉害,舌头在后座小声叫着,我们倒是开心地笑了。这种颠簸带来的晕眩,让人不由自主地快乐起来,我们喜欢这样的状态。
电台信号也随着颠簸变得不稳定,“…音乐会将在…举行,订票热线…8328”。随后,电台开始播放音乐,也是时断时续的,但我们听过这首歌,声音玩具乐队的《爱玲》。我们猜测那场音乐会也是声音玩具乐队的,因为昨天在潮湿俱乐部的时候,我们模糊听到旁边的男人说起他们正在巡回演出。也许他们马上就会来到城市的 live house,但可惜我们已经离开了,现在,我们只能在电台里听听他们的音乐。
走过这段颠簸的路,再往前就平坦了许多,两边的原野也成了树林。这倒十分反常,原野的道路应该比树林里的更容易修整维护的。我们猜测可能是重型货车不常经过树林,所以这里的路没被损坏。平稳也有平稳的乐趣,可是电台信号几乎遭到了屏蔽,没了音乐,我们能听到鸟儿和昆虫的叫声,偶尔还能听到林中小溪的水流声。车的发动机似乎成了这片树林最大的噪音源,我们开得很慢,但还是会惊动林中的鸟,它们一起飞起来,有时它们的粪便还会落在我们的挡风玻璃上。
从出发到现在,我们已经驾驶了三个小时,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这片树林的出口在哪儿。但我们很快乐,这种快乐不是为了让这个故事显得“酒神“而佯装出来的快乐。在一片夏天的树林里,我们亲近自然,但又在工业文明的移动机器里,刻意保持距离。我们像是隐形地经过这片树林,没有人看到我们,动物和植物也都是沉默的,除了后座的舌头。这是一种奇怪的安全感,对于正在逃亡的我们来说,这足以让我们快乐。
林中的路是蛇形的,经常要连续转弯。越深入进去,光线越暗。我们又这样前行了半个小时,突然发现右手边五十米的地方有亮光,我们以为那就是出口了。但路却向左拐,我们不得不下车走近去看,这才发现那是一片湖泊,大概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波光粼粼,像是遗失在树林里的宝石。虽然不是出口,但我们还是觉得幸运,这为我们带来了一次喘息。
我们从后备箱里拿出地图和帐篷,准备在湖边稍作停歇。林中的蚊虫太多,我们躲在帐篷里,将纱帐那一面对着湖水,又把舌头放在肚子上,准备这样欣赏风景。但手边的地图像是有股魔力,我们是在逃亡,但也是在迷失,我们都想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或者还有多久才能走出去。我们没有抵抗住诱惑,打开了地图寻找自己的大致位置。但是地图没有那么精细,我们处在一片模糊的绿色地带,其中的具体路线并未显示。我们只能安慰自己,还好林中的路并没有分岔口,它就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线,总有个终点。
这么想着,我们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我们昨晚一直没有休息,再加上驾驶的疲惫,再次醒来已经是下午三点了。我们从背包里拿出面包,就着可乐一并下肚止饿。湖面还是那么平静,偶尔有一条小鱼翻身跃出水面,然后再次消失。我们没有逃亡的经验,只想尽量远离某个地方,但有时也会想起杨万里的诗句:“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也许远离一个,又会接近另一个,我们总会败露。但现在这似乎还不必思考,我们还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日落以后,树林会变得危险,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我们把帐篷放回后备箱,又绕车走了一圈,发现车顶上有更多鸟的粪便。如果这辆车停在潮湿俱乐部的门前,肯定有很多朋友称赞它是一件了不起的装置艺术。在城市里,人们已经很少看到飞鸟了,当然也就很少看到这样的粪便。我们必须保持洁净,以展示出教养和礼貌。但一辆车的车顶满是鸟的粪便,却看不到始作俑者的踪影,这就像是一场荒诞的恶作剧,一种自然对工业文明的嘲讽。我们就在这种艺术里继续穿行,一方面是制造者,一方面又是被嘲讽的对象。
光线越来越暗了,我们都在幻想树林中发光的眼睛、凶狠的獠牙和锋利的爪子,这种场景出现在大多野外探险的纪录片里,黑暗总是带来躁动。我们彼此安慰路总要有尽头,但有时,我们又以为迷路了,似乎在绕着湖泊打转。我们不得不强迫自己相信那是湖泊的另一岸,或者是另一片湖泊。很难想象在这样的树林里,人类修造如此复杂又漫长的道路,这种环境更适合周末徒步,不局限在路上,而可以肆意穿行。正在我们快要绝望的时刻,车灯打亮了一块歪倒的路牌:距时代大道500米。
2 #
我们重新回到了公路上,那片树林像是抄近道时不得不去面对的屏障,我们克服了,现在电台也恢复了信号。天色已经完全黑了,我们在另一座城市的边缘继续前行,公路上的车非常少,两旁也没有灯火人家。在车灯的照耀下,公路看不到尽头,我们依然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地图上显示,我们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会抵达一座小城。但我们不能进城,我们要尽量远离那里,所以在某个路口,我们左拐试图离它越来越远。
到了夜晚,舌头变得越来越不安分。它从后座跳到了前排,又跳到挡风玻璃前走来走去。我们会突然打开雨刷吓唬它,它总是闪一下身子,再伸出脑袋上前打探。在潮湿俱乐部的时候,舌头可以自由活动,它是整个俱乐部的宠物,甚至是主人。它总是占据在最高的柜子上,俯看我们这些人聊天嬉笑,不知道它能否听懂,但有时我们觉得它只不过是在看一颗颗浮动的黑色发声球体。
大概了解到车内空间局促,舌头又跳回了后排。我们关掉了信号不良的电台,插上了一个闪存卡,随机播放着一些陌生的音乐。我们不再说话了,有时一起听音乐,有时各自想事情。我们一起做了一件坏事,现在又一起逃亡,我们不得不把彼此捆绑在一起。囚徒困境让我们相信彼此,又不敢抱以绝对的信任,所以我们像是在互相监视。我们必须以“我们”称呼自己,任何的你或我,都像是一种告密。这多少让我们没那么轻松了,车子最能感受到,它的速度时快时缓,像是我们的心跳时快时缓。
“我们不应该这么紧张的,我们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一件人们想做而未做的事情。在文明的词典里它叫做犯罪,但在正义的审判中,我们是获胜者。况且监控设备也被我们砸坏了,没有人能发现我们,我们的逃亡不过是一种自我的放飞,别忘了,我们是以酒神的姿态离开的。来,让车速快一点吧。我们不能喝酒,但我们必须体会晕眩。我们不能什么都不要,我们必须有所选择,要么是这样,要么是那样,我们不能同时都是。”
“你知道人们为什么喜欢潮湿俱乐部吗?在闷热的天气里,它的空调总是开到最低,又提供各式各样的冰镇饮品。在潮湿俱乐部门外,我们进去之前,是被汗水浸透的,在俱乐部里面,我们又泡进这些饮料,这也许就是潮湿俱乐部的名字的寓意。我们在那里什么都不用做,也不用去选择,那就像是一个冷酷仙境,我们可以在里面消磨一整个夜晚,和不同的人聊天,有诗人、记者、艺术家、素食者、同性恋、物理学家、宇宙主义者,我们总能从不同角度了解这个世界。我们确实不必两者都要,我们选择了一种,也可以同时接纳其他的所有。”
“我们不能后悔,人们都知道那不是一个仙境,它只是冷酷。夏天是闷热的,就像我们没有在车内开冷气,而是打开了所有的窗户,舌头也喜欢这样,它甚至探出脑袋来吹风。夏夜的风灼热但却流动,我们不能指望潮湿俱乐部也这样,除了那台联网的电视机播放着扭曲的新闻,我们的环境甚至是凝固的。我们没有必要再回去了,那里不值得留恋。事实上,哪里都不值得留恋。”
我们的对话经常以分歧告终,这并不代表我们无法理解对方,而是我们在理解过后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幸运的是,我们在道路选择的问题上没有争论不休,哪个方向、如何转弯,我们的意见总是出奇的一致。现在是午夜了,我们的车依然奔驰在看不到尽头的公路上,舌头也安静了下来。根据公路指示牌,我们推测我们已经距离城市四百多公里了。这多少让我们有所懈怠,车速开始放慢,我们仔细听起了音乐。
在唱片行业没落的年代,车载音响几乎都不再配备CD播放功能。即使是在潮湿俱乐部,音乐作为必不可少的氛围制造工具,黑胶唱片机也让位于网络音乐播放器。人们更多是把音乐存入闪存卡,这样更小巧也更方便携带,我们并不打算去复古,跟随潮流没什么大问题,反而是一味地保守在过去之中,会产生出幻觉。在潮湿俱乐部中,有位艺术家曾对我们说过,那些载体的变动是可以接受的,人们需要的是音乐,是音符通过巧妙的组合穿过耳朵抵达心灵,那些载体就像是地铁和巴士的区别,是可以为被选择被替代的。
我们听出了正在播放的音乐,Suede乐队的《Lost in TV》,我们也跟着一起哼唱。我们都不太擅长音乐,在潮湿俱乐部这个人才扎堆的地方,我们只是简单的宠物医生。我们被邀请加入俱乐部,是因为舌头在五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帮它做了绝育手术,并附赠了一个指甲修剪套餐,这让俱乐部成员打狂犬疫苗的比例大幅下降。俱乐部老板称赞我们有公共精神,而不是贪婪的利己主义者,所以邀请了我们加入。但大多时候,我们不过是在那里坐着,人们来找我们聊天,顺便聊聊他们的宠物。
3 #
尽管是轮换驾驶,但长时间的专注,导致我们越来越疲惫,腰和脖子都不太舒服。我们一路上都没有看到休息区,公路两侧也没有旅馆,我们只好继续坚持。撑到日出后,我们把车停在路边。清晨的温度刚好,我们又拿出帐篷,安置在路边。杂草上的露珠浸湿了帆布,我们不得不把舌头的薄毯铺在下面。舌头一副不情愿地叫了几声,跳下了车,也钻进帐篷。后备箱里还有一些饼干,我们已经十二个小时没有进食了,乏味的食物也变得好吃起来。
因为怕舌头跑出去,我们把帐篷的拉链都合了起来,但我们睡了三个小时后,被帐篷内的热气闷醒了。休息过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我们又吃了一些饼干,喝光了那一大瓶可乐。今天比昨天还要闷热,这样的夏日如果不吹冷气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不得不打开车内的空调,并期盼不远处能有一个加油站。我们出发时加满了油,现在快要用完了。
好在大约十分钟的路程,我们就看到一个加油站,有三四辆车在停车场上,阳光下那些车闪着光,仿佛随时都会爆炸。我们把油箱加满,为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付了现金。收银员一脸惊愕地接过钱,她说这是三个月以来第一次收到纸币。虽然笑着,但她还是打开验钞机,检查了一下纸币的真伪。确认无误后,她又对我笑了笑,我们没有多说什么,也笑了笑。离开加油站的时候,我们看到她从柜台走了出来,一个人站在门口。
我们又拿出地图,发现我们正行驶在一条通往沿海城市的公路上。我们故意绕开高速公路,而选择了那些疏于管理维护的公路,这让我们多走了不少路,但也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至少在高速公路上我们不能随意停下来。一路继续往东,再驾驶九个小时,我们到晚上就能抵达沿海城市。尽管我们执拗地要尽量远离城市,但海的诱惑很大,我们商量着在城市边缘的野海停下,海浪都是一样的,倒是海滩有所区别。
我们在潮湿俱乐部的时候,遇见过一位职业冲浪手,她告诉我们那些危险隐秘的海滩,会为浪花增色,有时甚至能在白色的碎沫里辨别出绚烂的色彩。不管职业冲浪手的话是否可信,我们终究确定了一个遥远的目的地,现在只希望一切顺利,我们可以安全地抵达那片未知的海滩。这么想着,我们意识到帐篷对这次逃亡来说无比重要,甚至提升了幸福感。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觉得不应该带地图,如今我们已离不开它了,因为我们确实有了目的地。
也许是闷热到了极致,天空开始变得阴沉了,我们能看到头顶的乌云正在不断堆积,酝酿着一场暴雨。这让我们有所期待又有所担忧,往后的每一秒,我们都在怀疑下一秒就会大雨滂沱,并做好了随时停车的准备。但半个小时后,我们离开了乌云区,才听到雷声从背后传来,我们暂且安全了。这在潮湿俱乐部也时有发生,经常是潮湿俱乐部所在的街区大雨临盆,而城市其他地方却日光明媚。不过在潮湿俱乐部里,隔音玻璃把雷雨的声响屏蔽掉了,我们只能听到音乐声、交谈声和窃窃的笑声。
像所有公路故事一样,我们也遇到搭乘顺风车的背包客,一位留着络腮胡的年轻男子。他的背包很大,大到可以装下十五只舌头。我们停车聊了几句,但显然我们不能载他,一是舌头霸气地占据了整排后座,二是我们的路线只有一小部分重复,而最为关键的是,我们要尽量减少与陌生人的接触。他们都是潜在的告密者,高度警惕地防备他们,不如让他们在路边等下一辆车。
这趟逃亡的旅途注定属于我们两个人,舌头绝对是意料之外的,我们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钻进了行李袋。我们没有为它准备猫粮,它只能吃一些我们剩下的面包或饼干,最初它是拒绝的,后来它还是悄悄吃了几口。我们甚至没有为自己准备足够的食物,因为带了现金,我们想着可以随时买到吃的,但事实上,一旦上路就很难停下了,况且沿途的商铺少之又少。这也注定是一趟不尽如人意的逃亡,带着窘迫和慌乱。从电影和小说里学到的“在路上”,绝对不足以应对真实的状况。在粗糙的环境中,我们都像是被文明驯养的羊羔,没有强壮的身躯和心智,只能凭借直觉和运气前行。
我们的车行驶在平坦的公路上,车玻璃把热气挡在外面,像是进入了另一个冷酷仙境。在这个日光刺眼的午后,我们朝着一片未知的海滩前行,在音乐的间奏里,我们偶尔幻听到人们尖叫的声音,警笛由远及近的声音,更多时候,我们听到的是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这种声音像是地球的呼吸,单调、反复、均匀又雄伟,也许我们看不出绚烂的颜色,但一定能够找到些许慰藉。如果我们不认为自己是错的,我们就不会用逃亡这样的字眼,如果我们有着充分的自信,我们就不会担忧。潮湿俱乐部不会为我们提供慰藉,我们想,也许那片海滩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