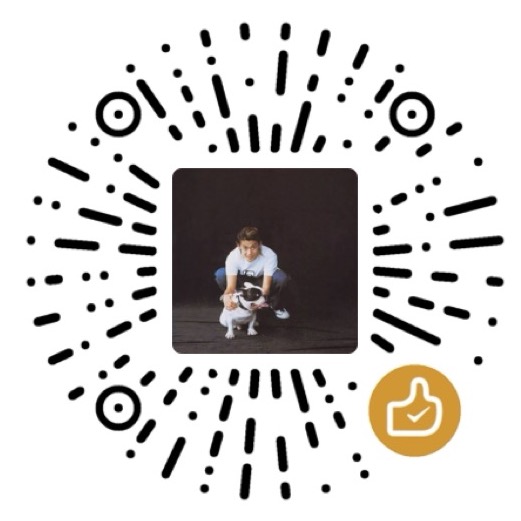被电视机制造的鬼魂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两次提到“空屋之声”,这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联想到日本电影《午夜凶铃》。电影中,名为“贞子”的鬼魂寄居在录像带中,观看的人在七天内会因诅咒而死,而破解的方法是把录像带复制给其他人。
这个电影很像“诅咒信”的变式,通过将诅咒信转发给其他人,来消除自身的危险。批量复制的诅咒之物,并未稀释本雅明式的鬼魂“灵晕”,而是为它提供了更多依附的媒介。
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电影最后,贞子披散头发、身穿白衣,缓慢地从电视机里爬了出来。为什么贞子必须从电视机爬出来?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并且始终没有找到合理的答案。
凭借我模糊的观影记忆和想象,恐怖电影里总是离不开镜子、照片、摄像机之类的物件。通常情况下,鬼魂是无形的,它们的显现需要借助媒介,也就是“附体”,比如灵媒或者布偶。即使是“空屋之声”,也为鬼魂提供了存在的场域。如果一个人可以直接看到鬼魂,那他大多是处于极端的精神状态中,难以区分幻觉和鬼魂。
换言之,鬼魂和人的交流是感应的、私密的,一对一的,但这种交流又是单向的、启示的,无回应的。因此,个体的经验描述,只能带来恐惧和猎奇,却很难提供说服力。
奥古斯特·孔德说,人类的组成中,死人比活人多。技术对已逝之物的储存,是对时间的反抗。长期以来,文字是亡者继续存在的唯一工具。而视听技术的出现,让人可以脱离肉体而显身,也让亡者再次复活,没有人真正地死去。当然,这仅仅是被记住,并不是作为鬼魂而存在。
奇怪的是,借助摄影机和留声机,我们确实捕捉到了这些鬼魂。在众多奇闻逸事中,胶片相机拍摄到了“多余”画像,摄影机录制了诡异影像,留声机的噪音夹杂了奇怪的话语,或者深夜电话铃响另一端的沉默。这似乎在告诉我们,技术突破了某种界限,带领我们进入了鬼魂的世界。
“留声机看上去像通向幽灵世界的大门”,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中继续写道:
记录性媒介使亡灵以新的方式复活再生。1877 年,《科学美国人》杂志对留声机做了这样的评论:“言语仿佛已经获得永生。”这里的所谓“仿佛”( as it were )就是鬼魂的栖身之所。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矛盾的操作问题:恐怖小说依赖人的想象,文字描述让人沉浸在一个自己吓自己的氛围;恐怖电影则依赖人的感官,画面音效共同实现了导演的惊悚目的,如果不展示鬼魂的影像,那么它何以成为恐怖电影。
我们要分辨清楚,恐怖电影不是灵异纪实,它和恐怖小说一样,来自创作者的编排,而非鬼魂的显现。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贞子从电视机里爬出来,是完全不同的。
尽管这部电影来自编排,但录像带在其中是纪实性的存在,电视机和我们观影的荧幕也是两样东西。录像带和电视机,其实是鬼魂对媒介技术的一种反向利用。镜头捕捉到了鬼魂,或者囚禁鬼魂,或者电影对鬼魂的展现的另一面,是鬼魂对技术的寄居。正如彼得斯所言:
每一个新媒介都是生产鬼魂的机器。
我们或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部分:在贞子从电视机里爬出来之前,还存在着贞子钻进电视机的过程。
在英剧《九号秘事》万圣节特别篇中,鬼魂没有爬出来,但进入了机器之中,甚至还改变了机器的运作轨迹,实现了驱逐闯入者的目的。它们并不是拒绝被捕捉的,而是甘愿去寄居,借技术显现,成为“ 机器中的鬼魂 ”( ghosts in the machine ),以此达到对人类的报复。
当然,无论是技术对鬼魂的捕捉和囚禁,还是鬼魂对技术的寄居和利用,都意味着技术和鬼魂的黏合,这是一种技术恐惧的表达。但这种表达未免小看了我们,我们不再因为纺织机的出现砸毁机器,也不再担心摄像机会猎取灵魂。这里必须存在其他解答。
站在无神论的角度来看,我想到了恐怖主义。大众传媒对恐怖主义的新闻播报,满足了节目的收视率和观众的猎奇心。但同时,这种播报也带来了恐慌,为恐怖分子扩大了影响力。恐怖分子通过大众传媒来散播恐惧,就像被要求复制的录像带和“诅咒信”,每一次复制都加强了恐怖的力量。和鬼魂一样,不是大众传媒捕捉了恐怖,而是恐怖在大众传媒中寄宿滋长。
不是贞子必须从电视机里爬出来,而是恐怖爬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