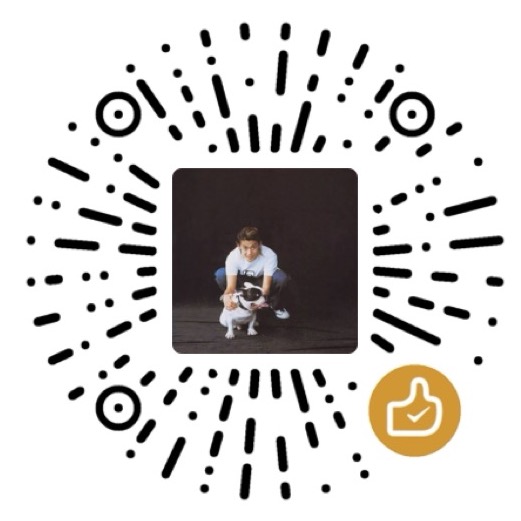钱多斯时刻与“第二手”存在
1 #
一次失败的考试,让你怀疑自己的智商甚至放弃学业。或者,因为某种漫不经心的语气,你对朋友丧失信心,最终质疑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可能。再或者,仅仅是“订书机没订书钉”,结果却变成你质疑职业生涯和人生道路的催化剂。
诸如此类的小事,在通常情况下,并不会导致我们宇宙的坍塌,我们只需要重新踏入正轨,就能继续前行。然而,在上面这些时刻,它们猝不及防,引发怀疑,却也可能带来一种“全面的失败”。
这就是“钱多斯时刻”:日常生活的某个寻常瞬间,突然遭遇存在意义的崩溃。
“钱多斯时刻”来自一篇《钱多斯致培根》的虚构写作,钱多斯爵士写信给弗朗西斯培根,描述自己职业的困惑,质疑语言表达的可能性,这种体验甚至引发了一种个体的生存危机,写作者不承认写作本身,进而否定自己。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也描述了类似场景。一个人“起床,乘电车,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四小时,午饭,又乘电车,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很容易沿循这条道路”。然而,突然某一天,他开始直面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继续活着?
这时,他就在经历“钱多斯时刻”,一个存在主义的时刻,也是被存在主义者经常提及的时刻。
加缪幻想西西弗正在怀疑推石上山的意义,然后提出两种选择:放弃,或是继续前进。如果选择放弃,那就是加缪所言的“自杀”,生理上的或者哲学上的。如果选择继续前进,神话不会被改写,西西弗接受了推石上山并没有终极意义——巨石终会滚落。
这就引发了荒诞,加缪把西西弗称为“荒谬的英雄”,并告诉我们,西西弗选择继续这么做,他会痛苦,但也可以是快乐的,我们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加缪有一种悲凉的浪漫,他分明在接受世界“温柔的冷漠”,却提供了一种反常的慰藉。
同样是面对“钱多斯时刻”,萨特和波伏娃却作出第三种选择。他们抛弃宿命论的观点,提倡对自由的追求,“你是自由的人,那就去选择吧——也就是说,去创造。”尽管道德规范和社会制度,或者你的心理状况或过往经历,都在指引着你,对你产生影响,但你依然可以冒险去做些什么。
2 #
这里不得不提起现象学,这是存在主义的思想渊源。胡塞尔不愿再去纠缠柏拉图主义,他提出“回到事物本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一杯饮料、一首忧郁的歌、一次兜风、一抹余晖、一种不安的情绪、一盒相片、一个无聊的时刻。它通过掉转我们自己通常如空气般被忽略的视角,恢复了个人世界的丰富性。”
存在主义也正是在肯定这种观点,它希望我们关注自身的生活,并在自身寻找意义。我想,如果萨特来改写西西弗神话,他既不会让西西弗放弃生命,也不会让西西弗服从惩罚,他会让西西弗离开这种生活,这种被给予的“第二手”存在,而去找寻自己的存在。
波伏娃是萨特的伴侣,他们维持着开放性的关系。我在一篇小说里曾对这种关系进行了另一种演绎,相较于他们的情感“契约”,小说中的两人却认为这是一种情感“宿命”,并将开放性关系视为对既定命运抗争的游戏。小说中的男主角以西西弗自比,但他的对应物不是巨石,而是那个顶峰。推动巨石,不过是为了抵达顶峰,这是他(西西弗)与其他女人(巨石)恋爱,却又与女主角(顶峰)结婚的隐喻。显然,这篇小说没那么存在主义,至少它的存在是“第二手”的。
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探索了女性气质的“迷思”,并认为“一个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逐渐长成了女人”。传统女性身份的建立,把家庭生活视为职业,来自于男权社会塑造的结构性压迫,这种压迫将女性看作男性的“他者”,导致女性看待世界的方式是“第二性”的,甚至看待世界的视角都可能是男性的:她不断想象自己在男人眼中的样子。
因此,波伏娃认为,如何成为一个女人,是最典型的存在主义问题。如果一个女性无意识地完成了男性设定的社会角色,她也许只是完成了一种“第二手”的存在。除了女权主义,存在主义还为同性恋权利、阶级壁垒的瓦解、反种族注意和反殖民斗争,提供了理论支持。存在主义希望人们追求自由、进行反抗,并且是在有主体意识的情形下去追求和反抗。
存在主义的观念和态度,已经深深融入了现代文化。电影、文学、电视,乃至报纸新闻,比如都市白领在周末参加禅修班,成功学暴政下的反成功尝试,逃离互联网六十天等等,这些散见在讯息汪洋里的“轶事”,其实都潜在地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
如今,存在焦虑还和技术焦虑相互纠缠。休伯特·德雷福斯谈论互联网,认为“其无限的连续性承诺要把整个世界都变成可储存和可利用的东西,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互联网抹去了事物的私密性和深度。所有一切,尤其是我们自己,成了一种资源”。我们通常认为的外在问题,其实都和我们的存在息息相关。
这就是我读完《 存在主义咖啡馆 》以后想说的。之所以是“第二手”存在,首先是我在这本传记和思想混杂的书里,用第二手的资料,间接地补习了“存在主义”。其次,所有循规蹈矩却又不自知的日常行为,都在告诉我,这可能不是我的存在意义,而是在社会“主流”的引导下,完成的一次“第二手”存在。
那些“钱多斯时刻”,我们是不能轻易无视的。它们也许就是我们的信号灯,从第二手存在,转向第二次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