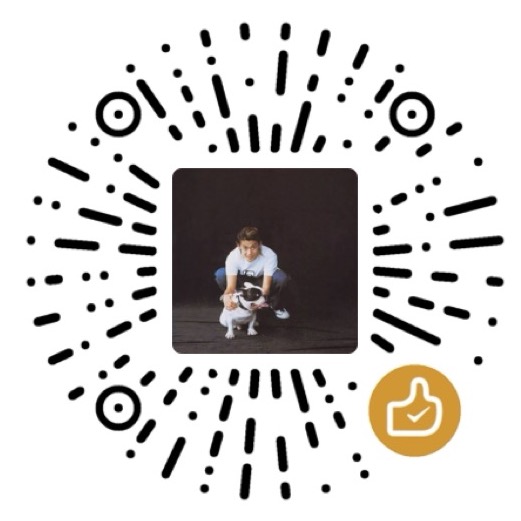海滩人与记忆癖
在《暗店街》中,莫迪亚诺提到“海滩人”。海滩人身穿游泳衣,出现在度假照片的一角或背景中,但谁也叫不出他的名字,谁也说不清他为何在那儿。甚至没有人注意到有一天他消失了。莫迪亚诺借角色之口说,其实我们都是海滩人,“沙子只把我们的脚印保留几秒钟”。
“海滩人”这个比喻,表达出的并非是个体的卑微,而是由于个体的卑微而导致的遗忘。
历史典籍记录王侯将相的酒会,但从不书写酒会上斟酒端菜的婢人,回望历史长河,我们看到的都是英雄伟人在河中泅泳前进,更多的人则像沙石沉在河底,无人过问。也许是因为历史总围绕大人物,即使是新闻这种“未来的历史”,也在努力寻找奇特和超凡。所以,现代人才会试图在主流与典范中寻找突破,转向对普通人的叙述。
学者佩克莱曾说:“我们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类学,一个真正关于我们生活的,不再是令人感到奇异的,而是细致和普通的人类学”。这种人类学的目的在于“描述每一天发生的事情:乏味的、日常的、显而易见的、普通的、平常的事,或背景噪音和习惯,以此来质疑我们耗费时间的方式和生活节奏,质疑那些不再让我们感到震惊的东西”。
对他来说,这么做的目的并不是去发现新奇的、壮丽的、震惊的、例外的和出乎意料的,而是要去重新发现或者认真看待,那些我们熟视无睹的事物,以抵抗时间流动带来的遗忘。这和历史有本质区别,历史是胜利者的宣言,记忆里则有每个人的叹息。
抵抗遗忘,就是记忆。普通人的记忆,成了历史学者或人类学者新的宝库。口述史、民族志、田野调查、非虚构写作等,不断叙述着普通人的故事。人们开始关注河底的沉沙,把它们一一捞起,淘金式地筛选和组合,找寻日常的传奇,建构历史的脚注。然而,文字绝非记忆最初的方式。
据说,“记忆术”最早由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发明,其原理是把记忆“地点化”,把需要被记忆的事件融入具体的环境,实现记忆与空间的连接。这种记忆术的核心在于“视觉联想”,按照西塞罗的说法,就是“选取一定的地点,把那些需被记忆的东西在头脑中转化为相应的图像,并把图像与选定的地点相连。这样,需被记忆的内容的组织结构便被保存在这些地点的次序排列中,而事物的图像则代表事物本身。”
这么看来,记忆术最早使用的媒介手段是空间化。这样的记忆是极度私人的,夹杂着断裂和间歇,以及对空间和事件的想象。而口语和文字的出现,则让记忆在口耳相传的传说和抄写转录的故事中代代相传。记忆从私人的脑袋里流窜出来,在群体内展示、交换与共享,成为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抵抗着权威的历史和可怕的遗忘。
再往后,经历了摄影、留声、录像,再到今天的数字储存,技术手段不断更新,记忆得以持久地保真。而人们也像是患上了记忆癖,借助技术工具,一丝不苟地保存着过去的印迹,毫无吝啬地展示着瞬时的记忆。个人记忆在社交网络上绝不存在,一经发布,它就成了共同的记忆重负。
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大量产出记忆,“我们今天所称的记忆,实际上是由庞大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材料累积和深不可测的资料库构成的”。待办清单越来越长,个人档案越来变厚,数字脚印越来越多,但记忆术的力量越来越薄弱,如詹姆斯·扬所言,“对过去纪念得越多,思考和研究反而越少。我们一朝给了记忆一个纪念形式,就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记忆的责任。”
记忆被记录了,也被搁置在一旁,记忆的功能病态膨胀,我们被挤向失去记忆能力的边缘。一方面,我们迫切的需要记忆的碎片来抵抗历史与遗忘,一方面,我们又背负着记忆的重担艰难行进。未来的考古学者回看现在,他绝对会皱起眉头,犯愁地爬梳着浩瀚的资料和无尽的记忆。
在那时,海滩人和海滩都会有自己的名字,只是名字太多,谁也记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