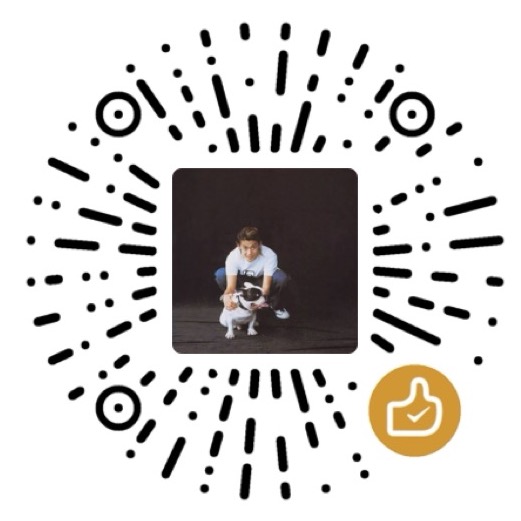想象的互联网
1989 年 3 月 12 日,万维网之父 Tim Berners-Lee 爵士递交了一篇论文,提出了万维网的最初设想。他想象 World Wide Web 作为一个公共平台,可以让人们在任何地方访问并分享信息,进行跨越文化和地理界限的合作。然而,近三十年后的今天,Tim Berners-Lee 爵士却对互联网失去了信心,他正在着手开发一个名为 Solid 的全新生态系统。
Tim Berners-Lee 爵士想通过这种方式开展自己的“互联网拯救计划”。在 2017 年,他在《卫报》上发表公开信,指责数据隐私、虚假新闻、政府监管和中心化等互联网病症,并认为“互联网系统正在瓦解”。因此,互联网拯救计划的目的就是“重新去中心化”,他希望人们重新掌握自己的数据,试图让曾经的设想“再次”变为现实。
这种想象具有公共精神,美好且引人入胜,但在互联网的崇拜者大批赶来以后,却在发生着变形。
“互联网是一个没有控制中心的水平式网络”,“互联网是独裁的掘墓人”,“互联网将造就一个明达、互动、宽容的世界公民共同体”…… 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充斥着大量关于互联网的乌托邦式言论,人们认为它可以创造出一个紧密连接的世界,帮助人们增进了解,培育宽容,促进世界和平,对经济、政治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言论带有技术崇拜的影子,就连互联网的英文首字母都被大写成“Internet”。这样的情形似曾相识,在大众报纸盛行的时期(1850-1887),自由派人士对报纸寄予厚望,认为报纸可以成为理性和道德灌输的工具,批量生产的报纸广受欢迎,具有改变社会的力量。
然而,这些言论并非基于证据,而是对互联网技术的演绎:因为互联网具有去中心性,所以它可以结束独裁实现民主,让弱小企业受到关注,让个体的人彼此连接,让信息不被垄断。显然,这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互联网的影响不是按照技术指令的单一方面展开的。相反,其影响经过了社会结果和过程的过滤。”
尼克·库尔德里就是一个对互联网持谨慎态度的学者。在《媒介仪式》中,他提出the Myth of the Mediated Centre,一种媒介化中心的迷思。他写道,万维网、移动电话和短信息系统等新的去中心化媒介形式正在成为主导,但无论这些新媒体有多大离心的潜力,它们时刻都可能被关于中心的迷思收编。也就是说,这种迷思缠绕着社会历史,以中心化为主体,宗教、王权或媒介都是其继承者。再极端一点地说,互联网的“中心化”不过是这种迷思的体现,是必然的结果。
事实也是如此,互联网的发展并没有按照乌托邦预言那样进行。前百度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吴恩达曾公开表示,产品有时不是为了收入而做,而是为了用户的数据。互联网已经“中心化”了,互联网寡头们分割着人们的注意力,数据和算法控制着信息流,这里充满着隐私泄漏、天眼监控和交流障碍,以至于程序员霍炬评价“互联网完蛋了,已经。”
具体到个人的交流上,技术的进步和交流的也并不完全同步。互联网作为一种便捷的媒介,曾被认为可以为人们带来海量的信息和广泛的连接,但事实上,它不能和传播的完成画上等号。在《信息不等于传播》一书中,多米尼克·吴尔顿说道:“如果只涉及技术,一切可能就会变得简单,而一旦涉及人和社会,一切就会变得复杂起来。”信息传递不仅仅的技术问题,传播活动也要比信息传播复杂得多。
我们可以这么想,互联网为传播活动提供了巨大的技术支持,图像、声音、影视、文字等信息可以进行跨越时空的传播,但“无法传通”的问题依然存在。这就说明技术可以有效实现“传播”,但不能决定“传通”,而如何传通更多的还是“人”的问题,这也是多米尼克·吴尔顿提到的“关系问题”。
如今,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和人们生活的“现实空间”,正在高度叠合交织。互联网已经成为生活的具体部分,是一种状态或方式,而不再是现实的倒影,不再是一种技术工具。如今,再把互联网视作一种工具,或者推崇为解放的力量,就只能是过时的观点了。无论你承认与否,我们的确是在数字化生存,也是在被数字化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