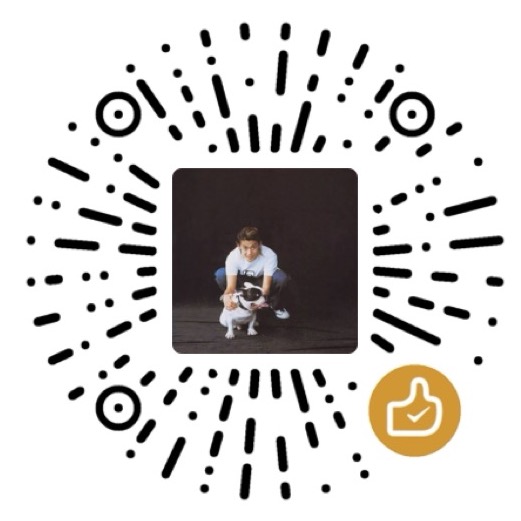我要赞颂的是一条尾巴
看周浩的第一部纪录片是《大同》(2015),他贴身拍摄一位中国市长,就像是一只“趴在墙上的苍蝇”。在他的镜头下,我看到了大同市的旧城改造,和这位被称为“耿拆拆”的市长的文化抱负。这部片子在豆瓣上是没有条目的,但是周浩这个名字让我产生了好奇。
我搜索下载了周浩的九部纪录片,每部都是八九十分钟,而且内容各有不同,自成一体。与《大同》相似的是《书记》(2009),周浩拍摄了一位县委书记。不同的是,《书记》是觥筹交错、莺歌燕舞的,更像是一个真实的官场。
《高三》(2005)讲述的是一段中国式青春,这里没有乐队、恋爱和自由的空间,有的只是做不完的卷子、打鸡血的鼓励和想要逃走的少年,每个经历过中国高考的人都会有所共情,因为我们都接受过这样的劝诫,以为会迎来所谓的“解放”,但过后只是新的开始。
周浩喜欢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观察流动的时间和流动的人。
《差馆》(2010/2011)有两部,连续两年春运期间,蹲守在广州站的警务厅,流浪者、小偷、丢钱的人、小商贩,在这里依次出现。在他的镜头下,差馆仿佛成了一座“教堂”,它调解、施舍、质询和惩罚。有个老实的男人一脸苦恼,因为怀疑朋友前来“认罪”忏悔,差馆还承担着告解和救赎的功能。
在《急诊》(2013)中,他来到广州市的一家医院,拍摄急诊室的故事,人们因为各种突发情况来到急诊室,或者120急救车随时待命出发,前往事故现场抢救。有的人因为喝了太多的酒离开了,有的人在下班路上出了车祸,有的人愤怒地吞了安眠药,有的人慌张逃走坠楼身亡。
《厚街》(2002)应该是周浩最早的片子了。
厚街是珠江口的一个小镇,各地打工者在这里聚集生活。周浩强调这些人们背后都有一个家,而这里只能算作是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的家在别处,也就会让矛盾更容易被激化:厚街的出租屋没有房顶,天南地北聚集在一起,抢劫打架时有发生。周浩只用零星几个镜头拍摄了打工者的工作,经济危机中大批工厂倒闭,车间里的机器和人都不在了。有一幕,两个男生拖着行李离开工厂,摔碎了他们的餐盒——一个隐喻诞生了,他们被解雇,“饭碗”也丢了。
看《厚街》时,我总联想到日本NHK拍摄的电视专题片《三和人才市场》。
《三和》的潜在逻辑其实就是《厚街》中的父母的留守儿童,长大变成了新一代的打工者。虽然他们都是外来的打工者,但不同的是,《厚街》里的人都是以家庭或亲密关系出现的,夫妻、情人、父母和孩子,而《三和》则是一个个孤独的人,他们更加“自由”和流动,想做拿钱快的工作。
他们的父母作为廉价劳动力纳入了全球化制造工厂,而三和大神虽然拒绝了这种劳累,却以一种隐形劳工的方式再次进入了,他们喜欢网络游戏,在网贷软件上借钱。他们的现实身份也十分脆弱,出卖身份证,生活在没有安全感的环境里。
周浩关心社会底层,也关注边缘人,他在《龙哥》(2007)中跟拍了阿龙,他吸毒也偷盗。片名英文叫做“Using”,其中也反复提到龙哥和周浩的关系既像是朋友,又像是在相互利用。有个情节是阿龙说自己吞了刀片,但后来他女友告诉周浩,他吐的血是自己用针管抽完饭进嘴里的。《龙哥》结尾,阿龙在高墙上行走,他转身对镜头说,我可以下去走的,但我是为了让你拍我,给你一个完美的镜头,这样比较好看。阿龙在镜头前,是一个自觉的人,与其说是周浩拍摄他,不如说是在自我表达。
最后一部是《棉花》(2014),温情的配乐压过了田地的野风、嘈杂的人潮和轰鸣的工厂,也让纪录片的力量减弱。周浩拍摄了棉花的产业链,从棉花的种植,到纺织再到加工成衣服,在博览会上出售。农民和打工者在漫长的劳动中,透支着体力,他们希望自己的辛劳可以换取生活的改善,希望下一代离开土地和体力劳动,这不是对土地的背弃,而是在市场经济下土地和粮食作为初级产品的薄利,而农民和打工者承担了其代价。
也许是因为周浩是记者出身,他的主题非常敏锐,很像调查报道的视觉化。现在流行的非虚构写作,很大程度上也在做着同样的描述。但是,非虚构写作看似事无巨细地讲述或呈现了一个人、一件事和一个问题,但很多时候都会进入到自我陶醉的情态之中,讲究文章布局和细节。而对于阅读者来说,动辄上万字的长文也是一种压力,纪录片反而更加直接了,影像的力量也更为强烈。
周浩在《厚街》里说,我们不能用“苦”或“不苦”来形容他们的生活,他们离开农村来这里赚钱,生活的酸甜苦辣在这里上演。爱人的纠缠、家庭的慰藉、离别的不舍,爱当然也存在于他们的生活,这是和所受教育与社会地位无关的,似乎是一种本能,他们也许爱得更加深沉。
不管人们身在何处,都有着欢乐与悲伤,所谓的“怜悯”很容易沦为一种俯视和猎奇,却忽视他们本身的感受。说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来承认他们的快乐,但同样,也必须追问“安知鱼之痛”,否则就是对眼前诸多问题的遮蔽和美化,最终也就变成了自我感动,我们的情绪被释放了,却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