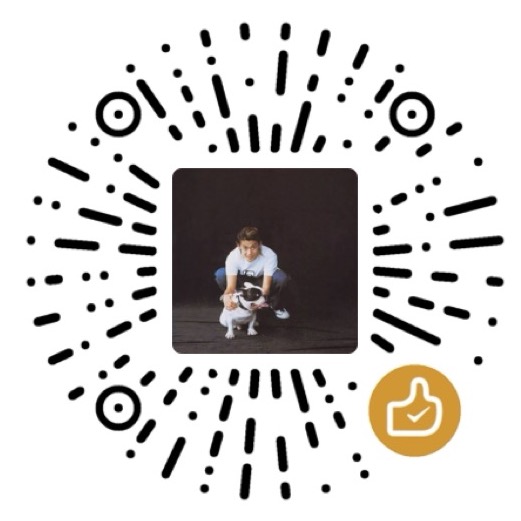野草莓
这个季节的风总是在夜里忽然撞上玻璃,如果我不小心给窗户留了缝,它就会带着嘶鸣的怒意钻进来,把我从梦里叫醒。我必须睡眼惺忪地起身,在昏暗中探测拖鞋的位置,然后关紧窗户,轻轻地,以免吵醒熟睡的西西。她总是把头蒙在被子里,冬天的时候她希望借此取暖,现在她为了保持一种不被打扰的姿态。我在一篇小说里写道过,尽管“哈扎尔辞典”认为熟睡的时候乃是一个人最为脆弱之际,但显然在清醒时刻,我们更容易被击溃。西西睡着,暂时地离开世界,我在黑暗中仿佛成了一个守夜的卫兵,保护她的安全。我清醒着,不管是因为窗外的风,还是口干喝水,我都被留下来了。窗户紧闭的房间一片阒静,我赤身裸体,没有武器,这是击溃我的绝好时刻。
即使到了白天,风依然没有停歇的迹象。我从六楼俯看槐树,坚实的树干稳固地杵在街道两旁,柔韧的枝叶却被风任意摆布,羽毛球和风筝被吹落了,塑料袋又粘上来,叶子被抖去微尘,别的灰土又来重新染色。我怀疑每一棵树都长成了风的形状,每一个人都长成了境遇的模样。西西和我的意见相反,她对我诉说昨夜的梦,梦里她在等候地铁,她需要在地下漫长的穿行,从一端去往城市的另一端。她不知道那趟地铁何时到站、开门,她何时才能走进去并占据一个心仪的位置,她甚至不知道她要去另一端做什么。她说,人在做梦的时候会丧失感官能力,比如她不能借助听觉去判断,只能站在空荡的隧道旁,向洞穴深处打望,猜测地铁是不是要来了。
地铁最后来了吗?我问西西。她说,地铁当然没有来,但这种无名的、纯粹的、义务性的设置,却让她明白了自己还可以做出别的选择。什么选择?我们离开窗户,坐在沙发上依偎着。她说,她像是忍无可忍了,但分明没有挣扎,她离开了地铁站,从地下走出来,外面的世界光亮刺眼。你知道吗,在地下待了太久,你就会不适应地上的风景,如果我等到了那趟地铁,迎接我的将会是在黑暗的隧道里无尽的穿行。可那是梦啊,绝不是我乘坐地铁在地下穿行,而是一趟地铁整夜穿过我的大脑。我问,你昨晚有感觉到我起床关窗户吗。西西摇了摇头,她把右腿抬起来,日光洒在她白皙的皮肤上。我伸手抚摸那些光,它们仿若静止。那天以后,西西消失了。
1 #
我去往我们经常吃晚饭的餐馆,试图寻得蛛丝马迹。这个餐馆是我和西西相识的地方,它位于英雄广场的东侧。从地铁站3号口出来,刚好可以看到雕像的背面,如果是下午五点,我们会笼罩在雕像落在地上的阴影之中,只要朝阴影的头部走,就能到达餐馆的门口。这是后来西西告诉我的,一种奇特却又浪漫的识别技巧,并且这像是唯一一种抵达方法。如同爱丽丝需要兔子引路,如果不这么做,就难以找到餐馆,毕竟我第一次去这个餐馆时,就迷路了。
那时,我约了方野一起吃饭,他总会提前到达,所以即便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分钟,但一想到被人等待,我就产生焦虑感。这种情绪无助于我的寻觅和判断,我提前一个路口左转了,曲曲折折,哪里都不是我要赴约的地点。我还在使用旧款的翻盖手机,没有智能地图可以帮忙,我不得不去询问坐在路边的一位阿姨,她包裹在驼色的毛呢大衣里,眼神恍惚,反应迟滞,像是生活在另一个季节。我把问题重复了三遍,她才明白我的意图。阿姨把手从大衣的口袋里掏出来,指了指,让我返回到主路上继续走。
因为以上原因,尽管我本来还有十分钟,但最终我却迟到了五分钟。按照我和方野的规矩,我需要帮他誊写十首诗,如果你有所 了解 ,应该知道他的灵感如此破碎,诗句更是杂乱,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折磨。后来我的确完成了这项惩罚,但直到此刻,我再次来到这个餐馆,那些诗都没有问世,用方野的话来说,“诗人写诗的数量,不能超过诗人的岁数,所以我必须缓慢”。我们各点了一杯生啤,他便开始了他的讲述,和谁相遇又分离,如何熬过沉闷的夜晚,怎样处理一地破碎的玻璃,以及安抚一颗汹涌的情人的心。
终于他讲到了这个餐馆。他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这里,只是觉得这个餐馆具有某种植物性,必须定期光顾,以照看它是否鲜活地生长。这是诗人的语言,我并不觉得它和什么植物之间会发生关联,即使有,也是植物的终结之所。餐馆主营炒菜,符合我的口味,背井离乡的人需要通过食物唤起乡愁,保存一丝与过去的联系。我难以形容这种从味蕾到记忆的短路式的触击,它像是一根针,轻易戳破了我维持已久的自大的气球。
我和方野约定下一次见面,还是在这个餐馆。再见到他时,他的身边多了一个女人。女人的耳朵上悬着两个巨大的银环,在餐馆的灯光下一闪一烁,等她坐在我的对面,我才把注意力转向她的脸。“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我的脑海里掠过维米尔的画作,她们都有着一副神秘的面容,欲言又止,等待着发问。“我是西西”,她先张口了,我来不及发问。
“西西来过吗?”我问餐馆的老板娘,她摇了摇头,然后说道,我上次见到西西,就是你和她一起来吃饭的时候了,她怎么了。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可以用“消失”这个词语吗,或者更委婉一些,“不见了”可以吗。我只好撒个谎,我们闹别扭,她跑出来了。老板娘说,你的诗人朋友呢,他好久没来我这里了。我说,他可能在忙着创作。老板娘说,也许你可以问问他。我说,我联系不上他,一般都是他主动联系我。老板娘说,你去他家找找。
这个建议带有植物的滋味,我能体会到老板娘的潜台词,她把西西和方野联系起来了,但这显然是臆想。我像往常一样,点了杯生啤,老板娘送我一盘花生,我说喝完再去。她笑了笑,就去招呼别的客人了。透过日暮时分的玻璃门,我看到英雄雕像的阴影盖住了门外的街道,猫蹲坐在树下,也许是早已习惯了人来人往,它格外沉静。如果西西在的话,她会像往常一样,上前抚摸它,并从包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猫粮。她有自己的宠物哲学,猫没必要专属于一个人和一个房间,它的世界应该和我们的一样宽广。
我突然把手插进了口袋,潜意识里我认为里面会有猫粮。确实如此。也许西西之前穿过这件衣服,或者是她偷偷放进来的。我打开玻璃门,风还在肆意刮着,猫扭头看向我,起身走了过来。我蹲下轻抚它,它发出舒服的呜呜声。我把猫粮放在手心,它粗糙地舔食。我起身准备回去,它悄悄跟在我的身后,像是要我再陪它一会儿,或者是要告诉我什么秘密。
2 #
我意识到西西消失了,是在我从英雄广场散步回家之后。通常情况下,我会在晚上十点独自去广场散步,半个小时可以绕广场走三圈,随后我进入广场旁的便利店,只是看看,就像在家里打开冰箱那样,看着货架上摆放得整整齐齐的商品,我会感觉安宁。这么说来,便利店就像是城市的冰箱,抚慰着漂泊的人。但西西总会有别的看法,她说,便利店的敞开看似温柔,却是无差别的“爱”,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些什么,恰恰说明这种爱的普遍和普通。
我们不能用普遍来掩盖特殊,我说,即使对所有人都有爱,但我所体会的情绪是和我自身最为相关的。西西接着反驳,那不就意味着“你”更具重要性,便利店则是一个投射对象吗?你常去的英雄广场也是一样的吧,便利店提供安定,英雄广场则制造孤独。但对某些人而言,便利店是消费欲望,英雄广场却带来自然状态。我无能为力地说,我去英雄广场不是为了享受孤独。
那为什么总是独自却不带上我,西西问道。这应该不算是什么秘密,尤其是在西西消失以后。自从和西西认识以后,我就停止了小说写作,在艺术创造中,西西这样的女人通常都会扮演“缪斯”的角色,她为我提供灵感,把我的生活浪漫化,让我的笔触再次充满感情。但是事实上,三年来我没有写下一篇故事,曾经想象力占据我的大脑、梦境和脚步,如今我只体会到现实感。一个男人在遇到一个女人以后,不得不去面对的现实感。这种现实感把我从文学的世界,拉回了生活的世界,而英雄广场则是我的“过渡地带”。
我听说英雄广场上的雕像是重修的,它的影子曾出逃又被捕捉回来。这不是魔幻的故事,而是在都市报上被记述的新闻。对我来说,英雄广场和孤独没有关系,它只代表着一个还未被祛魅因此充满魅力的地方,这是小说滋长的沃土,是空间化的缪斯,是离开现实的大门,是专属于我的“过渡地带”。我沿着广场边缘散步,如同一只狐狸进入法阵汲取魔力,我想收获的不过是一丝灵感的火苗。但它总被扑灭,不管是被这个季节的风,还是被那种嚣张的现实感。
因此,西西不能和我一起,否则她和英雄广场之间的张力,会把我撕裂。这么说来,我的写作无比矫情,一个女人的吻就会将之毁灭。我从英雄广场回家以后,发现西西不见了。她的衣服、照片、杯子、化妆品,和她的行李箱一同消失,我只在枕头和浴巾上找到几根她遗落的长发。我从窗户向楼下巡看,没有踪迹,拨她手机,没有响应,连忙音都没有,我又给方野联系,他是我们唯一共同的朋友,同样无人接听。我又检查了一遍房间,西西连一封诀别信都没有留下。
西西消失了,过去的三年如同真空,这让我无比恐慌,但又不能报警,种种迹象表明她没有危险,这个“消失”是她主动进行的。她会去哪里呢,这座城市里她的朋友不多,我试图在通讯录里找到什么人,也许能从中获得什么线索,最终都徒劳无功。我又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她的场景,她的耳朵上悬着两个巨大的银环,在餐馆的灯光下一闪一烁。后来这对银环还在我的房间里闪烁,在英雄广场的灯光下闪烁。我又重返英雄广场,这时候已是午夜,空旷的广场上耸立着一尊巨大的雕像,西西不会喜欢。
当我离开餐馆又告别了猫,我还是去了英雄广场,那晚重返过后我就没再接近它。沿着雕像落在路上的阴影,我反过来向广场走去。这条路是我和西西最常走的路,她总是哼着《永远的微笑》,脚步轻盈,仿佛我不紧紧牵着她的手,她就会随风飘走。日暮时分的英雄广场热闹非凡,相比夜里十点,这里毫无魅力,不过是城市的一处公共空间,昔日英雄的光辉继续照耀着善忘的后人,只有它的阴影照耀我。
我低头看了看,雕像的影子还在脚下,像是从没有离开过。随着夜色和影子融为一体,我又像是回到了神秘的世界。西西的事情被我短暂放在一旁,我的触角慢慢伸出,谨慎感知着空气、人群和雕像。我提前开始了我的行走,在广场绕行三圈,结束的时候,在按部就班走向便利店的路上,我看到了西西。她在店门口微笑着看我,像是一直在那里等我。不,我以为我看到了西西。
3 #
我整夜沿着广场漫步,或者说,广场的人行道整夜穿过我的大脑。从梦中疲惫地醒来,眼前是西西消失的第三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反应并不那么合乎常识,没有躁动不安的情绪,也没有歇斯底里的找寻。像是遗漏了什么东西,我只是在去过的地方检视,餐馆、广场、便利店,但都一无所获。还有一个地方,餐馆老板娘曾提醒过我,方野的家,我分明是不屑一顾的,却又有些许迟疑。我又拨打西西的电话,还是没有响应,方野也是一样。
西西第一次跟着方野来见我的那个夜晚,我们就交换了手机号码。方野也在场,他似乎乐意看到这样的情形,后来还专门写了一首诗《给人鱼》——就像乐手喜欢用音乐记录情绪,他喜欢用诗句隐藏故事。
你的故事让友人落泪,于是这颗星球被水包裹着,并一直那么咸。口渴的人更渴,寻爱的人相继死于爱。你一直在海岸回望,方向错了。我一直不愿走,失去犯错的机会。我和你不同,但其实我应该是你,你应该比我自由。
他把那首诗给我看的时候,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捕捉到了正确的含义,西西是那条人鱼吗?我是那个友人吗?到底是什么故事?我需要遍寻自己知道的一切,去匹配这些密码一样的文字。
“你和西西怎么样了?”在我破解诗的咒语的时候,他问道。“我们最近经常见面,一起约会看电影。”“什么电影?”“昨晚我们看了《奇爱博士》。”“嗯。虽然我看不到,但我知道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不是院线片,所以我和西西在家一边喝红酒,一边看电影。我们经常如此,不管是前面的约会时期,还是后来的同居阶段。西西并不算是电影爱好者,但她很乐意和我一起看,偶尔她躺在我的怀里睡着,我会把声音调小,继续看完。
她消失之前的夜晚,我们又看了一遍《奇爱博士》,两周年的纪念电影,去年我们也看了。这是很让人困扰的事情,我们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谁也没想到我们还要看第二遍,接着是第三遍。如果它足够有趣,我们倒是乐意,但这种纪念仪式无比枯燥,仿佛重复阅读电器说明手册。然后,她忍无可忍关掉了电视,“我们应该换一种纪念方式,不能永远地重复,每年都回到同一个地方”。
“我们换一部电影?”我已经想出了其他十部适合纪念之夜的电影。“不,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去做些别的事情。你知道的,我没那么喜欢电影,我宁愿没有发明电影。”西西显然说的是气话,但我听出了她的含义,对于纪念之夜,我确实没有花费心思考虑。这也许是她消失的原因?她并不是这样草率的女人。那么,消失已经蓄谋已久?我竟然丝毫没有察觉。方野似乎早就提醒过我,西西是神秘的。
于我而言,西西同样如此,她很少谈论过去,但总是畅想未来。这个未来里有我、一只猫还有一座花园,仿佛我们不用吃饭、睡觉,却总要在花园里晒太阳,以及和猫玩耍。她说,我们可以邀请方野来做客,我们把不同的花朵摆在他的面前,让他用鼻子辨别出每一朵花的名字。我们也可以让他帮忙照看猫,他太孤独了,需要一只猫陪伴左右。他最近在忙些什么,你要不要去他那里看看他。
如果这是我写的一篇小说,主角是必须要去那里的。不管方野在不在家,不管我在他家里看到什么,我都需要给小说的读者,或者说给我自己一个交待。按照作家们的套路,西西也很大可能会在方野那里。这时候,我会死心,接着后知后觉地发现过去的种种细节。比如,西西在我散步归来的时候,慌忙挂断了谁的电话。又比如,我和西西认识之前,她为什么和方野在一起。这些细节像是为我自己摆脱嫌疑,我在整篇故事里都是一个清白的受害者。
然而,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生活戏剧化,事实也是如此。
4 #
我站方野楼下站了很久,才等到一位女房客打开楼栋大门。我趁机进去一口气爬到顶楼,轻轻敲门,无人回应。我又拨打电话,隔着铁门传出一阵铃声,无人接听。方野也“跟着”消失了吗?西西不见了,方野也不见了,老板娘的暗示也许成真。我的脑袋里想象出无数的可能,每一种可能又被另一个代替或推翻,乃至我似乎永远得不到答案。或者说,我本以为我和真相只是相隔一道房门,但如今,我发现中间是层层叠叠的藩篱。
现在是午后两点十八分,我看了看手表,这并非一个心碎的时刻,而是一个失落的时刻。我缓慢地一阶一阶下楼,打开楼栋大门,按照作家们的套路,天空开始飘洒细雨。我不擅长哭泣,雨水和泪水混合的情节难以生效,这些雨滴只好钻进我的眼睛,冒充成我的泪水。不仅失落,这还是一个戏谑的时刻。随后,方野出现了,他戴着墨镜,独自坐在楼下的长椅抽烟,头顶繁茂的大树留出了一片避雨区。
“我终于见到你了。”我坐在他旁边,像是一个久别重逢的朋友。他递过来一根烟,我从口袋里摸出打火机。“你最近在忙什么?”我没有直接问他西西的事情,“我怎么都联系不上你。”方野回答,“我和女友争吵分手了。心情太糟糕了。但讽刺的是,诗句却整夜乱蹦,我写了一些新诗。编辑正在整理。”我说,“我为你誊写的那些,是不是也要发表了。”他点点头。“那你和女友为什么争吵?”“没什么,恋人们常做的事而已。”他描绘得云淡风轻,心情似乎转好。
“也许是因为 对面的女人 。”方野继续说道,“我听女友说,我房间窗户的对面,住着一个常常偷窥我的女人。不久前,我和她第一次对话了。她说晚上好,随后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那些问题像是巨石压在她的胸口,我没有力气帮她挪开,我的木杖也无法帮她击碎,我只好给她念一首诗,一首写给西西的诗。”他终于提到了西西,甚至为西西写过诗。“后来,女友告诉我,那个女人的窗户再也没有打开了。她消失了。”
“这座城市总会有一些女人莫名消失。”我借此言彼。“没错,但我很担心那个女人。她的问题我给不出答案,她眼中的我和我想象的她,只是在两个窗前隔空偶遇,然后分离。”“西西也消失了。”我终于说出了这句话,然后扭头看向方野。“怎么了?”“我从英雄广场散完步回家,她和她的衣物都不在了。后来,我去了餐馆、去了广场,寻找她的蛛丝马迹,但都一无所获。她联系你了吗?”方野摇了摇头。
“最近她都没有联系过我。上一次,也是三个月以前了。她打电话问我喜欢什么品种的花朵和猫咪,说我非常需要一只猫的陪伴。还问我最近在忙些什么,是否有空我们一起去餐馆吃饭。”我想起那次通话了,在我搪塞说方野在写诗并且不愿去看他以后,西西给他打了电话。讽刺的是,我心里的石头也悄悄放下了,至少西西不在方野这里。“我实在想不到她会去哪儿。我们之间热恋如初,什么理由可以让她毫无预兆的消失呢。”
这座城市总会有一些女人莫名消失。他重复我的话,这是这座城市的特质,仿佛有什么不可名状的暗洞,悄悄吞没了她们,但城市却保持着平静。“我们应该去寻找这些女人,还是去寻找暗洞?”我按灭了烟头。“不,你把暗洞具像化了,它是弥散的,如同空气。你不可能找到它。”他也按灭了烟头。“那只有继续寻找西西了。”“为什么你不能接受她的离去,就像你接受她突然的到来。”
雨越下越绵密,我想起了西西的梦,她从地铁站出来,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我又想起我的梦,我整夜绕着英雄的雕像散步。梦里她去了光亮的地方,我在暗色的广场兜转,现在她消失了,而我还在记忆中翻找寻觅。我想她一定是乘着地铁离去,在地下漫长的穿行,她的耳环闪烁银光。我想此时此刻,总有一个男人在城市什么地方继续等待,因为总有女人在什么地方一个接一个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