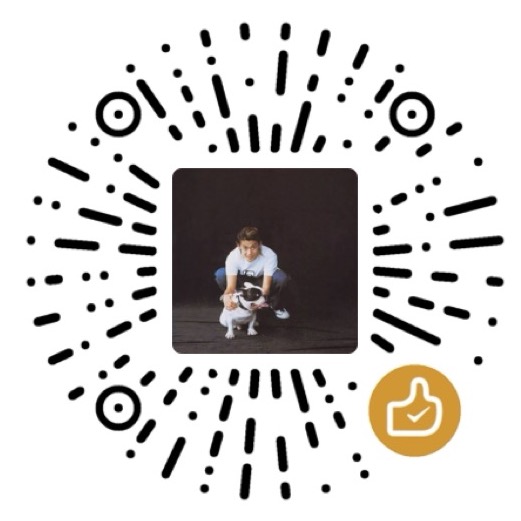退化
工作之后,每天敲击键盘写的一篇篇文稿,都是谋生的差事,那种主题内容和表达方式会影响一个人。公文的写作是冰冷的,让我在除此之外的写作上,失去了想象力。我已经写不出那些探索性的、呼之欲出的、灵光乍现的文章,也不再那么迫切地想要在小说的写作中隐身,曲折地表达。工作没有彻底让我成为社畜,而是把我改造成为一个机器,完成任务的写字机器。如果被问及我是否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回答是肯定的。工作为我提供物质养料,每月20号准时发放的工资,就是我出租甚至出卖自己的酬劳。但工作让我精神贫瘠,琐碎的事宜正在构成一个琐碎的我。
我还是会想去记录些什么,比如这次漫长的春节假期下,整个社会生活的停滞,而酿成这桩悲剧的绝非一个传染性较强的病毒,它就像是一道难题,测试的是我们如何去解答。李文亮之死也不是一个英雄的坠落,而仅仅是一个普通人,被压垮了。他的死亡是一种普遍的死亡,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被训诫又被利用。显然,解答漏洞百出。千城一面也不仅是外部的楼宇、商场和消费景观,武汉可以是任何其他的城市,李文亮可以是任何其他的人,是我们。
我的父母是从1月18日从武汉回来的,在我的催促下买了口罩,又在我的监督下居家隔离。感染人数每天在增长,隔离期也从12天扩大到14天,他们本来初六可以结束,又继续熬到了初八。那种禁闭式的生活,无比压抑。新闻报道中的春节喜讯和疫情进展交叉地映现在眼前,我们定时吃饭,经常睡觉。期间我甚至陷入了自我怀疑,因为我的体温有些上升,后来觉得消化不良,在快结束时甚至如鲠在喉、呼吸压抑。结果无非是自己吓自己,他们安然无恙,我也从巨大的压力中释放,身心一下子轻松,再也没有什么不适。也许是习惯了这种隔离生活,即使过了隔离期,父母也没有出门意愿。连日的新闻正在恐吓、改变他们,病毒仿佛就在门外,他们只有在家才是安全的。
他们平安,对我而言是幸运的,但我又无法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人间地狱”并不是虚幻,而确实正在发生。物资总是短缺,慈善组织总是出错,人民的互助仿佛是活下去的出路,而社会管理太过不堪。我仿佛看到切尔诺贝利事件重现了,首先是谎言,其次是集体动员,最后是光荣胜利。活下来的人庆祝活下来,死去的人自始至终都在沉默。我希望这场疫情不至于摧毁我们的生活,它可以帮我们看清哪里出了问题,需要我们去纠正。这注定是一篇自我阉割的文章,因为我已经退化到不会说话。